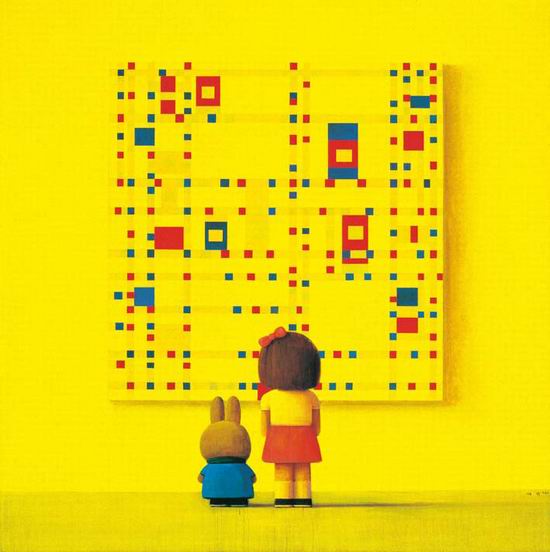洪再新:文人画研究的普世意义
http://www.socang.com 2011-12-21 11:16 来源:中国收藏网
二十世纪的艺术和学术史表明,追求中国艺术的普世意义这个终极关怀,文人画的研究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逐步成为认识表现主义艺术的新范式。
洪再新
研读台湾美术史家石守谦教授的新著《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自然会想到他1995年出版的《风格与世变》 (该书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简体字本,并改副题为“中国绘画十论”) 。第一部论文集,将绘画风格的分析,结合着形成这些风格的重要历史语境,逐一检视,让读者认识到不同画面所传达的时代和社会信息。眼前这部新论文集,仍然重视绘画风格的分析,并以此为起点, 在中国画的历史长河中,反思这些不同风格的人文蕴涵(即作者所说的画意),使绘画的题材和观念的讨论, 落实在具体作品的创作和鉴藏过程中。两部论著共同的特点,是作者在某个时段,围绕其总的思路来研究不同的个案。由此展开画史重建工作中的整体与个别的关系,瓜熟蒂落,结集成书, 体现出一个学人在探索中国美术史过程中形成的通识观。
自我意识与文人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性
这部新著,连同导论“从风格到画意”, 共十六篇文章,分“概念的反省”、“多元文化与文士的绘画”、“绘画与文人文化”、“区域的竞争”和 “近现代变局的因应”五个单元。它的副题为“反思中国美术史”。仔细一看,其重心落在文人绘画上。为什么作者如此强调文人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性?
显然, 这和石先生的写作环境分不开, 特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对历代文人画的保存与研究历史有内在的联系。台北故宫的藏画向国际学术界开放,直接引起了1960年代对宋以后文人画研究的热潮。加上没有遭遇在大陆出现的“文革”那样的浩劫,所以保持了它研究的延续性, 取得了丰硕成果。石先生《风格与世变》和新著中的个案研究,正是和这个学统一脉相承的。文人的自我意识,是“画意”的成熟形态,它通过文人的主动选择,将绘画的风格在特定语境中发挥其功能。
在第一单元第二篇界说文人画时,石先生认为它是一种理想形态,因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永远的前卫精神”。1920年代初大村西崖和陈师曾在提倡文人画复兴时,尽管注意到同一时期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却只能点到为止,未及展开。石先生看中文人画的“前卫精神”,对我们重新审视老大师及其名画巨迹,颇多启示。譬如,他注意到六朝-唐宋时期和“大师传统”共存的“主题传统”、元代“文人画谱系”的意义、明代中期主流与非主流绘画的关系、 明中叶以后文人画家职业化的现象,诸如此类,均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流画家走在时代前列的独创性,以及同时代画家围绕着其独创性所作的连锁反应。其中,第三、第四单元的两篇个案颇有代表性。
第一篇是讨论董其昌(1555-1636)在春秋鼎盛之年为同乡布衣陈继儒所作的《婉娈草堂图》(1597年, 台北私人收藏),兼具风格和画意两个议题。石先生将画家此际的生平活动与受画者当时的处境互为参照,重现出董为松江画派选择的学习样板的具体实践。从风格上看, 董其昌对他所崇尚的前代山水名作进行了高度的抽象, 创造出他以笔墨结构作为山水主体的个人面貌。这种抽象性, 常和西方现代艺术之父塞尚(1839-1906)的结构表现并提,而在时间上早出两百多年。因为在1590年代, 董以“朝服山人”的姿态, 在南北各地观摩研究书画藏品, 一方面提高眼界和画艺, 一方面形成他的“绘画南北宗”理论。他与隐居不仕但心气相通的陈继儒共同提倡新的艺术运动, 挑战主盟画坛多年而日趋衰落的吴门画派。正如董1628年题同乡沈士充《长江万里图》(上海博物馆藏)云:“吾松画道自胜国时湞溪曹云西及张子正、朱寿之,之后无复嗣响。迩年眼目一正,不落吴门习气,则自予拈出董、巨,遂有数家……”石氏指出,《婉娈草堂图》超越了元代以来文人画传统中“书斋山水” 或“山斋图”,强调了“对实景的转化,意味着对此部分的文人画传统的刻意逆反……《婉娈草堂图》的创作,由这个角度观之,亦是董其昌这个‘朝服山人’超俗之心灵世界的呈现”。这样的“画意”对松江画家的召唤力是颇具影响的。
另一篇是分析十七世纪金陵绘画由奇趣到复古的风格演变。金陵画派的存在是个松散的社会现象,缺乏所要直接超越的对手。不同画家力图通过绘画来表现现实,并游离其外。所以金陵画家的奇趣和复古,既是风格的特征,又是画家创意的体现。面对这样复杂的时代中的复杂问题,石先生以明清换代作为分界,拓大了高居翰1971年组织的《不安的山水:晚明中国绘画》展览的时代下限。又在晚明松、吴、浙等诸多画派区域竞争的格局中,检视江山易色后社会阴影笼罩下金陵画家的作品,如“国变后的金陵与其怀旧画风”、“由感伤至复古的转化”和“趋向一统中的金陵复古风格”的特点,重现出导致画风变化的创作语境,丰富我们对十七世纪金陵画史这一切面的深刻体认。
上述两个案例以地方画派的形成和发展来显示《绘画与文人文化》和《区域的竞争》两大主题之间的关系,将风格到画意的转换,落实在董其昌的一件杰作与金陵画史的一个切面上。高居翰1976年曾在《明清绘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风格》一文中提出“风格也是观念”的重要假说。但其文末一段话认为,后期的中国画家因为极其专注于画风而对绘画主题失去了兴趣,以致“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后期的绝大多数绘画和其中大部分精品,都没有主题”。1989年高居翰在为该文中译本写的按语中提出修正,宣布放弃这个观点, 并在后来的研究中非常注意像“诗意画”和“世俗画”这类主题。石先生这两个案例,恰好就对明清绘画主题(画意)做了正面铺陈,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忧患意识与艺术史写作的当代性
《从风格到画意》以近现代画史殿后,和开篇的理论思考彼此呼应, 把从六朝以降的绘画, 放到近现代研究中国绘画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考察, 呈现出艺术史写作的当代性。
关于当代性, 石先生在“导论”和第五单元第一篇“绘画、观众和国难”的讨论中, 对二十世纪学术史上“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回应”之流行的认识模式提出质疑,有其深刻的思考。在中国艺术史和艺术史学传统之外,近代的中外关系,构成了我们认识和反省自己传统的一个关键。石先生拈出“国难”的话题,是以国家的概念来看处于战争与动乱状态中的社会,审视艺术家和艺术传统在此时此刻的境遇,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深重的 “忧患意识”。
在“导论”中,石先生谈到海外收藏中国画的历史。在欧洲中国艺术史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en)系统收集整理出版古代中国画之前,西人只是以欧洲绘画的经验形成对中国画的表面印象。国人因为 “国难”当头,只是将此印象匆匆拿来作为参考。上世纪中叶以后, 这一局面开始改观。这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例如,对女性艺术史最深沉的反思,是在毛泽东时代。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国际学术界的女性研究方面,代表了一流的水平,不仅回应了美国学者林达·诺克林1971年提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的假说,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文人画史的探讨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石先生在“绘画、观众和国难”的论述中没有谈到齐白石,也未将他归入文人画家的行列。原来每一具体的个人对待“国难”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齐白石就是一例。据朱万章《齐白石艺术与日本的传播及其他》一文(刊于《齐白石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下],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齐白石在与一日人的合影相片背后写道:“白石七十八岁,日友平岛君合照,戊寅春(1938年)。买画之朋友。此君最快爽,绝无一点繁琐。”这和以往所谓齐白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闭门谢客的传闻颇有出入。说明靠卖画为生的齐白石, 在战事爆发之后的北平, 没有脱离国际艺术市场的影响。
“国难”一题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美术和美术史学在近现代所经历的处境。从石著的第五单元上溯到第二单元, 蒙元时代对于汉族文人而言也是国难当头的岁月。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文人画谱系的确立意义重大,以确保中国汉文化传统的延续。石先生书中收录的文章,发表的时间前后跨度近十五年,原有各自不同的写作语境。尽管如此,他在字里行间却表达了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形成其鲜明的个人性, 成为其新著的看点。
文人画情结与中国艺术的普世意义
石先生的文人画情结,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文人画的普世意义。这要求我们在研究文人画的历史时, 努力探寻其在艺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此, 我们可以从他新著的书名来作分析。就像他前一部文集的书名, 此书也以风格问题为出发点,表明风格在艺术史探索中无法回避的重要性。艺术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的这个玄机,既使人困惑,又让人神往 ——“风格之谜”永远考验着艺术史家的学术识见。因为包含有图像与文本两部分的艺术史细节,使所有个案和综述研究都不能不在事实与价值判断两方面齐头并进,缺一不可。石先生的苦心见诸《从风格到画意》书名大标题的英译(From Style to Huayi)。此一画意,借用传统语汇成一专有名词来处理“理论构架与风格分析的关系”,并以拼音huayi来替代intention(意图)、iconology(图像学)、theme(主题)等西文术语。
石先生本人出自西方艺术史学的主流学派,即以潘诺夫斯基 (E. Panofsky)开创的普林斯顿学派。他在第一单元第一篇,提出了“对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再现论说模式的省思”, 实际上要回应的是艾尔金斯(James Elkins)在《作为西方艺术史的中国山水画》一书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中的一系列假说。后者的基本论点,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绘画研究,由于受整个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 只是西方艺术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是石著重点意在突破的理论难关。
在近三十年的艺术史实践中,石先生注意到了“运用风格分析,尤其是从‘归纳’ 推至‘演绎’时,在中国绘画史领域中操作上的局限性”。究其原因,这和以德语为母语的西方艺术风格史研究的参照系有关。石先生很早曾撰文《中国绘画史研究中的一些陷阱》(收入石守谦等编著《中国古代绘画名品》,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要人们警惕落入风格解读的局限; 他的新著的重点,是在既往的风格研究套路——例如乃师方闻在《心印: 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中所建构的叙事模式——之外, 做不同的尝试。该书导论中“画意之见” 一节,引出了和风格理论直接相关的深层问题:
如果不以“再现”为依归,中国绘画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呢?它有那样的最终目标吗?
石先生称此为“不容易简单回答是否的问题”,有他个人的理由。他推崇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E. H. Gombrich)等西方艺术史学泰斗的学术理念,也始终面对着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史学对中国绘画研究的影响。如果否认这一影响,就是否定石先生个人、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研究史。他毫不讳言,受贡氏《艺术与错觉》一书的引领去“一窥风格史的堂奥,Gombrich也就成为我的学术偶像。再接着,我又读到Panofsky那篇《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名文……发现了艺术里头珍贵的‘人文意涵’之确实存在,也让我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画史书中常常提到的‘画意’概念”。
这段自述,帮助说明 “画意”的一般意义。问题在于,文人画在千余年的艺术史上,通过《从风格到画意》的研讨, 可以得出什么总体印象来?换言之,石先生的深入个案工作和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考,是否有助于我们探寻中国艺术的普世意义?相信该书的读者会各有心得。
近代以来的世界艺术研究,已经把中国绘画(包括文人画)作为人类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 艾尔金斯的论证只讲了近代西方美术史学发展的一个面向,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中国艺术中那些具有普世意义的成分,已经和正在改变“世界艺术”的总体面貌。例如, 日本的南画复兴,有一个基本的参照,那就是新兴的德国表现主义。而日中在复兴文人画的努力过程中,又反过来推动了欧美各类现代派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二十世纪的艺术和学术史表明,追求中国艺术的普世意义这个终极关怀,文人画的研究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逐步成为认识表现主义艺术的新范式。
责任编辑:邹萍
- 推荐关键字:洪再新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中国收藏网的立场,也不代表中国收藏网的价值判断。
在售藏品
相关新闻
- ·诸家之言:评论王冬龄书法艺术
- 2011-08-19
- ·江苏泗洪出土新石器人类遗址 距今8000余年
- 2011-07-06
- ·首届中国画双年展学术论坛把脉当代中国画出路
- 2011-04-02
- ·赏贵金属纪念币上的滕王阁(图)
- 2011-02-23
- ·首届中国画双年展杭州举行“当代中国画”的处境危机成焦点
- 2011-01-18
- ·把脉当代中国画出路
- 2011-01-07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