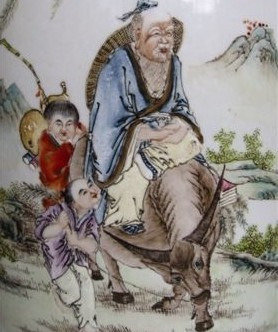可以说,梅摩报告分析的基础是拍卖数据的金融化运算,与以往艺术市场行家建立在感觉经验上的认识完全不同。但也正因为如此,《岳敏君报告》的分析也应停留在数据分析上,给出结果即可,不必做脱离数据分析之外的其他解释。而该报告所犯的最大错误即在于,在不了解艺术家市场真实成交情况(主要是行家所掌握的客观数据之外的其他信息)的基础下,试图从数据分析进入到对艺术家市场的具体分析,这样的分析必然是牵强附会的。
试看《岳敏君报告》对岳敏君市场各阶段的解释:
“2000年,岳敏君试探性地送拍了第一件油画作品,以13.2万顺利成交,使岳敏君的油画在二级市场有了初步的定位,但后续3年只送拍了2幅作品,而且流拍,或许可以理解为其作品的藏家还没有系统性地为进入拍卖市场做好准备。”
“2004年……当年送拍的3幅岳敏君作品全部成交,给买卖双方增添了信心。2005年,送拍数量增加到4幅且全部成交,无论上拍量还是成交量都在不断放大。”
“经过试探和放量阶段,岳敏君油画市场的买卖双方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买方渴求岳敏君的油画作品,卖方希望通过拍卖市场寻求回报,都做好了进入市场的心理和资金上的准备。”
“2007年,共有10件千万级作品诞生,全年成交金额高达3.74亿,超过个人成交总额的一半(截止2011年春拍)。这些数据足以说明2007年是属于岳敏君的一年。”
“由于岳敏君的作品在欧美市场备受追捧,而金融危机对欧美造成的影响更为惨痛,所以此次岳敏君油画行情的下跌幅度显著大于整体走势。”
“从总体来看,岳敏君选择的市场推广路线和国际化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很多方面的成功经验都值得新晋艺术家学习。”
这些解释充斥着无根据的推理、想当然的猜测、没必要的结论,甚至出现了对想象中的买卖双方的心理分析。这些解释不仅没有对证明其观点提供任何帮助,反而暴露出撰写者对岳敏君市场真实状况了解的严重不足。这样多此一举、不值一驳的解释一再出现在整篇报告的不同章节中。
问题三:行文空洞的学术分析
在《岳敏君报告》“代表作品价值分析”一节中,除了“价格分析”、“现值分析”两类建立在指数分析基础上的客观分析之外,还包含一段“重点作品分析”。这段选择了《轰轰》、《希阿岛的屠杀》、《大天鹅》3件有高价成交记录的作品进行孤立的“价值分析”,试图从艺术价值的角度对3件作品做出学术性的判断,然后再描述其市场表现,来说明它们在学术和市场上都得到了肯定。
首先,这样“赏析式”的文字不该由标榜“数据分析”和“客观方法”的“梅摩艺术指数研究中心”来撰写,如需证明岳敏君的学术价值,大可引用评论家对岳敏君艺术价值的相关论述,若没有针对具体作品的批评文字,直接略过即可,报告中单独对重要作品所作的赏析显得很突兀。
其次,对3件作品的文字阐释流于表面,仅停留在描述画面构图的层面,对每件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独特价值均未涉及。策展人顾振清(微博)先生在转发微博时写道:“对岳敏君高价作品学术分析的行文较空洞、八股。”在《岳敏君报告》中还提到岳敏君“参加数量众多的国内外重要展览”,而实际情况是与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相比,“重要展览”正是岳敏君的软肋,在对中国当代艺术起关键作用的几次展览如1979年“星星美展”、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1993年开始在香港及欧美巡回展览的“后89中国新艺术大展”、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1994年的圣保罗双年展等等都与岳敏君无关,2007年UCCA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也不包含岳敏君。此外,岳敏君也没有足以奠定其学术地位的重要个展。
再次,我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对岳敏君各系列作品的分类分析,因为艺术家不同时期、不同系列、不同材质的作品,在市场的表现往往各不相同。遗憾的是,《岳敏君报告》仅分析油画作品,不涉及装置、雕塑,但就在油画作品中也没有细加分类,都笼统的冠以“岳敏君作品”之名。对岳敏君“傻笑”系列之外的“处理”系列 、“场景”系列、“迷宫”系列一概忽略,避而不谈岳敏君转型作品在市场上折戟的事实。而实际上,对于市场上的标杆艺术家而言,转型的失败直接关乎其未来市场的信心。
五、数据分析方法论存在的问题
梅摩《岳敏君报告》发表后,我们征求了一些业内人士的看法,不少人都认为分析方法没有什么问题,也有人认为方法永远不会受关注。但对于出具艺术市场分析报告的机构,研究方法是首要问题,因此我们仔细研读了《岳敏君报告》及其他梅摩报告。我们认为,梅摩艺术品指数研究中心在数据分析的方法论上,也存在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梅摩指数的根基。
问题一:金融模型的先天缺陷
每一种金融模型自诞生之日起就都带有先天缺陷,梅摩指数也不例外。梅建平教授认为根据艺术品的特点如尺幅大小等设计的指数有很多缺点,因为不可能涵盖所有重要的因素,他在《梅摩指数的基础与方法》一文中说道:“艺术品的销售实际上和房地产的销售是很类似的,因为房子也不是买了之后马上就卖的,也是住一段时间或持有一段时间再把它卖掉。到底持有多长也是随机不确定的。因此我就用房地产指数的方法来做艺术品的指数,然后把它建立在同一件艺术品多次拍卖的基础之上。”
梅摩指数采用的是房地产价格指数模型中的“重复交易法”(Repeat Sale Method),该模型的优点是基于同一宗房地产的价格变化,在剔除标的物折旧的影响后,不同时期相同房地产的内外部品质等都相同,根据重复交易法编制的指数可以满足房地产价格“同质性”的需要。
这一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对比与中国油画市场,可得如下表格(左列资料据全球最大中文经管百科网站“MBAlib智库”):
问题二:原始数据来源不完备
据《岳敏君报告》附录2:“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对岳敏君历年所有油画拍卖记录进行统计、有效性筛选后计算得出的。目前的统计周期为半年,即每年拍卖市场最活跃的两个时期:春拍(01.01-06.30)、秋拍(07.01-12.31)。所有统计数据仅限于艺术家的各类油画作品,不包括其他形式的作品。本文中所提到的价格,除了着重指出的,计价货币均为人民币。”
这是全文唯一一处对原始数据来源的介绍,至少有3点未明确说明:1.数据的来源是哪里?是拍卖公司官网,还是来自雅昌艺术网等公开提供拍卖数据的媒体?2.如何保证可以囊括岳敏君“历年所有油画拍卖记录”?3.“有效性筛选”的标准是什么?
《岳敏君报告》开篇“2011年春拍综合分析”一节统计出岳敏君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共上拍10件岳敏君油画,成交率为71.43%,总成交额为18,539,036元。我们据此推算出梅摩统计的岳敏君2011“春拍”油画总数为14件,而据我们统计,这一时期共有18件岳敏君油画上拍,其中伦敦菲利普斯、伦敦佳士得、伦敦苏富比各上拍1件,首尔拍卖在香港上拍2件,见表7。根据梅摩报告计算的总成交额推算,梅摩可能漏掉或“筛选”了3件伦敦拍品的其中2件以及首尔拍卖香港上拍的2件,但我们看不出有何理由需要对这4家国外拍卖行的拍品进行筛选,更可能是梅摩报告遗漏了其中4个记录。
另外,梅摩指数以每年1月-6月为春拍、6月-12月为秋拍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方式合适纽约、伦敦的拍卖,但与国内的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油画及当代艺术的春秋拍起止点应以每年4月初香港苏富比春拍和10月初香港苏富比秋拍为准,把1月-3月划入上一年的秋拍、7月-9月划入同年春拍,更符合近几年中国的艺术市场周期。
见微知著,我们有理由质疑梅摩艺术指数研究中心搜集原始数据的严谨性及使用方法的科学性。
问题三:样本数据的真伪存疑
数据最大的问题不是来源是否完备,而是样本量不足、样本量是否具有代表性、样本本身真伪的问题,先来看看梅教授的理论和设想。
还是在梅教授《梅摩指数研究中心:中国艺术品市场成为新的资产类别》一文中写道:“在很多油画的拍卖中都经常出现虚伪交易(假拍)。而这种情况也跟早年中国股市操纵价格和虚假信息泛滥的情况非常相像。为了摆脱这种价格操纵的假象,我们采用了金融经济学中的办法,排除或降低了虚伪交易或其他形式的价格操纵的交易对数据的影响。我们的方法论是基于2005年美国《金融经济学杂志》77期上姜国麟、梅建平、Mahoney的关于股票坐庄的学术论文。”
梅教授2011年11月5日发表的《艺术市场指数是如何编制的》一文中又写道:“所谓坐庄就是虚假交易,不是真实的交易,因此即使拿到了拍卖数据也还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梳理一下,把一些明显的有托儿嫌疑的数据剔掉一部分,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市场交易的情况。具体怎么来剔除,这是一个比较高深的学问。”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我们无法看到梅教授所提的这篇论文,但我们找到了2007年8月发表于《新财富》杂志的署名“梅建平”和“姜国麟”的文章,标题为《借鉴股市经验规范艺术品市场》,文中建议:成立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中央艺术品登记公司(简称中央登记公司);根据拍卖公司的诚信记录,由中央登记公司按分级标准给予定级,拍卖公司在其等级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并向中央登记公司缴纳保证金;在国家的监督指导下,在全国各地成立艺术品鉴定机构,每件艺术品需经独立鉴定后方可拍卖;建立退赔制度,若由艺术品鉴定机构出示证据说明拍卖品为伪品,成交后的第一年内可按原价退还,佣金不退等等。从这篇文章能看出梅教授对中国未来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一些过于理想化的构想,可惜文中没有详细论述“股票坐庄”及如何剔除假拍。
巧合的是,刊登《岳敏君市场分析报告》(下)的报纸上,同时也刊登了梅教授一篇名为《如何规避“托儿”和赝品》的文章,虽然没有提供明确的结论和详细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根据原文,可以归纳大意为:作品如果在好的拍卖行“传承有序”就能很好的规避赝品,文章开头则提出“足量的交易可以减少指数被人操纵的可能性”,并详细论述交易量不足的指数极易被人为操控:“比如说你有家具收藏,你想操纵这个指数,因为指数里面交易不是很多,你拿出一件家具交易一下,找几个人来托一下,拍一个天价出来,由于这里边的数据不是很多,突然来一个很高价的就可以把指数抬高了。抬高了以后,如果指数被报道的话,就会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觉,就是中国的家具涨得很好,大家都来买家具,你就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收藏抛出去,这样指数就有可能存在被人操纵的情况。”
我们认为,无论客观的数据分析还是感性的经验判断,都只能作为辨别“假拍”的辅助手段,成交的真实情况只能依靠从最接近真相的人或机构处获取可靠的信息。而根据《岳敏君报告》的统计,岳敏君油画的总上拍量为166件,曾重复上拍的仅25件,在我们看来,这一数量应属于梅教授认为的“交易量不足”、“极易被人为操控”的范围。中国油画拍卖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开始,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真正兴起不过5年时间,除少数成名较早的艺术家在二级市场上已站稳10年以上外,大部分艺术家才刚刚经历第一轮市场周期的考验。其中绝大部分人的上拍总量不超过500次,重复拍卖作品件数不超过50次。
对于梅摩指数这样一个建立在单件艺术品重复交易记录数据上的分析体系,所能找到的中国油画的匹配数据在现阶段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只有几十组甚至几组这样数据的艺术家而言,这样的研究方式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
更站不住脚的是,仅有的一些样本又可能存在数据真伪,也即“假拍”问题。我们并没有看到梅摩报告设计出行之有效的规避中国当代油画假拍的研究机制,这从《岳敏君报告》只字不提作品假拍情况可见一斑。该报告将岳敏君拍卖成交价最高的10件作品视为“最受市场欢迎的油画作品”,认为“这类作品不仅受到了艺术界的好评,更是广受收藏界的关注,以至于不断刷新拍卖纪录”,这显然是建立在假设这些作品全为真实成交的前提下的一个很表面的推论。事实上,整篇报告也都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对了解市场环境的行家或其他专业人士而言,必然没有任何说服力。因此有博友在梅教授微博上留言:“方法论与研究过程的确新颖。但倘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不论过程怎么准确严格,结论也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顶层》2009年1月号发表的《顶层评估报告: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曾梵志》一文中,我们曾判断:此5人在2007、2008年间的市场走势曲线是人为修正的虚假曲线,由于2005-2007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让持有资本的炒家炒作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心理预期提前了,本来应该在未来启动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此期间迎来了第一波行情。这一判断是我们综合比较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股市大盘曲线、当代艺术市场走势,并经过推理论证得出的。此后随着我们与艺术圈的接触越来越深入,对所评估的5位艺术家市场的看法开始渐渐分化,如果再一一重新做更具体的评估,会有很多新的看法。但我们对“虚假曲线”的判断,却一直在不断得到各种信息的佐证。因隐私关系我们无法公布信息源,这一判断仅限读者参考。
我们认为,可靠的信息来源、深入的现场观察、专业的数据分析,是甄别拍卖假成交的三种有效手段。可惜,我们并没有从该报告中看出梅摩研究团队掌握前两种手段。如果纯粹从数据分析,依然有可能察觉出假拍的蛛丝马迹,如作品底价落槌、重复上拍的对比等等,但该报告也未采取这种具体的研究方式。
梅摩指数试图建立一套以客观数据为基础的,解释和判断艺术市场走势的金融理论和计算模型,但多数理论和定律都是包含限定条件的,脱离限定条件,现实中的人为或偶然因素会造成很大的干扰。如果置原始数据的真伪于不顾,再自洽的理论和模型也只是沙上之塔。
问题四:现值分析的含糊之处
《岳敏君报告》虽然给出了很多建立在其指数模型上的数据,但对于“梅摩中国当代油画指数”和“梅摩中国油画岳敏君指数”两个最关键的数据却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方式。文中出现的“现值”、“现值区间”、“当期价值”、“市净率”等概念,都是通过原始数据与相应指数计算而来。尤其是“现值”,在报告中多次被使用。
经济学意义上的“现值”,一般指在给定的利率水平下,未来的资金折现到现在时刻的价值,是资金时间价值的逆过程。时间是有成本的,预期的现金需要等待的时间越长,其现值越小。绝大多数对“现值”这一概念的应用,都是针对未来的,而梅摩报告中“现值”的概念则是针对过去的,是“利用梅摩-中国油画岳敏君指数将作品当时的拍卖价格进行折现算出作品现值”。未来的收益才能折现,以前拍出的价格如何“折现”?
姑且认为这里的“现值”依然有用,但梅摩报告对现值的分析仅有一段文字,从几个表格中的“现值区间”的数据与作品当时成交价来看,其中的关系并不明显。我们认为,此处才是最能体现梅摩指数独特价值的部分,可惜该报告在不必解释的地方乱加解释,应该详加说明的地方却惜字如金。
报告下半部分又引入了两种“市净率”概念,依然建立在“现值”基础上,依然只对结果做了解释,而未解释得出结果的关键步骤——如何“通过指数折算”。
问题五:西医中医各自为阵
做艺术市场金融分析模型的不止梅摩一家,但梅摩指数的引用度和知名度相对较高,研究成果传播较广,今后任何一家仅立足于数据分析的模型,都将遇到梅摩指数所遇到的问题。
目前的现状是,学金融出身的人和学艺术出身的人都对自己的专业性过于自信,或者说对对方的知识领域认知有限,互相难以说服,而最好的艺术市场分析方式是将两者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如何结合,又取决于统筹者及执笔者是否对艺术市场及金融理论都有深入的理解,同时在表述上兼顾艺术与财经语境的专业性。
借用梅建平教授的话,应该中西医结合,否则偏科症必然影响分析的准确性。当然,由于现实环境中,各方利益的牵连,以及对话语权的争夺等实际因素,很难让中西医走到一起。
六、重复拍卖的简单逻辑
对于重复拍卖,我们与梅摩指数的看法有很大差别。我们也认同重复拍卖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但遵循的逻辑却没那么复杂,常见的几种有效的判断方式如下:
(一)、重复拍卖估价低于此前成交价,则此前成交有假拍嫌疑:如曾3次上拍的岳敏君2002年作《天空·动物·人》,在2007年香港佳士得以216万元成交,到2008年北京保利秋拍却以140-180万估价上拍,若底价售出则比上次成交亏损约33%,虽然最终268.8万元售出,但却又在2010年亚洲联合秋拍上以155-210万港币上拍,底价低于两次的成交价,且最终流拍。何以两次委托人都愿意以“亏本”估价卖出,不排除前面“作价”的可能。
(二)、短时间内换手快,则艺术家市场有投机泡沫:如岳敏君2000年作《向丹顶鹤同志学习》,2007年6月24日在北京翰海拍出504万元,3个月后的2007年10月7日,又以400万港元的底价出现在香港苏富比秋拍,成交价为794.35万元。这种“春进秋出”或“秋进春出”的情况并不鲜见,往往发生在某个艺术家市场上涨的过程中,持有者希望通过短线交易赚快钱,往往交易品种有一定质量但不会是艺术家的顶尖精品,持有者对其长期升值潜力并无信心。
(三)、天价拍品再度出世,则艺术家市场有见顶趋势:艺术家拍出几千万天价的拍品轻易不会再度露面,除非几种可能:艺术家行情走高即将达到这一周期的顶点,或艺术家行情持续走低,再不出手可能会被牢牢套死。如今年苏富比秋拍张晓刚《大家庭一号》即为前一种情况,春拍时张晓刚作品创新高,到秋拍是出货良机。岳敏君《希阿岛的屠杀》、《画家和他的朋友们》则为后一种情况,岳敏君行情持续低迷,再不出货可能情况会更糟。
另外,还需注意同一幅画换一个名字上拍,这种情况以过世艺术家的赝品居多。岳敏君有一张2003年作《黑云》,2008年春拍在香港佳士得拍出577.38万元,今年春拍在香港佳士得再度上拍,名字换成《非典》,估价150-200万港元,172.42万元成交,重复上拍后的价格缩水近70%,虽然赝品的可能性很小,但也值得揣摩。
七、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岳敏君作为曾经的中国当代艺术四大天王,其市场神话已经完结,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一线艺术家阵营的首个出局者,其作品不再具备担任天价交易品种以及投资品的可能,其作品价值将因流拍和滞销而大幅跳水,但作为有较高知名度、识别性及一定市场基础的艺术家,岳敏君作品短期内也不会很快退市,但其此后的市场价格将被打上一个很大的折扣。
本文对梅摩艺术指数研究中心《岳敏君报告》一文的不同意见,主要针对其明显错误的结论、逻辑混乱的解释、失去根基的假设,而对于梅摩采用的金融分析方式,因报告本身未透露核心细节,我们也难以作更深入分析。对于兴起不过五六年时间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而言,任何有志于从事分析报告撰写的机构都是初学者,也请梅摩指数研究中心对本文的错漏不吝赐教。
- 推荐关键字:市场分析报告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顶层》评估报告:看跌岳敏君(图)
- 2011-11-24
- ·上万文产项目入户深圳文交所
- 2011-05-16
- ·中国艺术品市场需从速建立全球观念
- 2011-04-08
- ·中国艺术品市场世界第一有水分(图)
- 2011-03-31
- ·艺术市场走向反复无常的新时代?(图)
- 2011-02-10
- ·艺术品市场由“暖”转“热”成为又一投资选择
- 2009-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