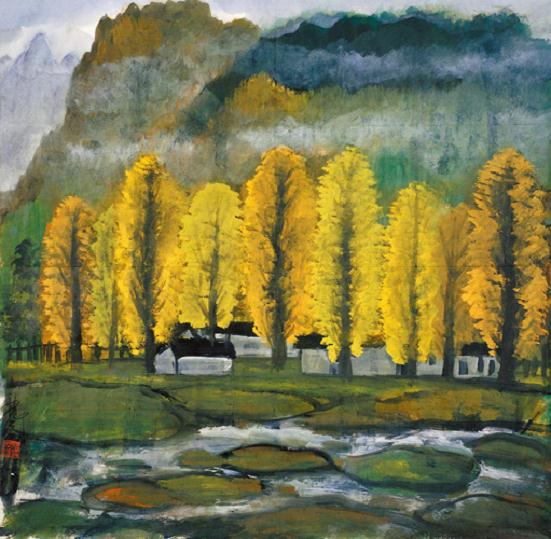一个和Alfred Clark及大维德齐名的玫茵堂藏瓷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腾空而出。
他背后不是只有一个“玫茵堂”主人的代名词,而是有一群人。这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遇到了“玫茵堂”主人,并与之结下不解的藏瓷情结。
50多年以来,“玫茵堂”主人不断将中国瓷器收入囊中,其中以清三代为最,并将对中国艺术的热爱和敬畏深埋心间。
现在,它成熟了,接着前人的步伐,开始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场中走秀,而那位曾经指引“玫茵堂”的前人及其子仇大雄所珍藏的犀牛角也一并亮剑。
最重要的私藏
2011年4月春拍,香港苏富比推出的“玫茵堂”珍藏专场一直备受瞩目,早在一个多月前,各大媒体上就铺天盖地都是“玫茵堂”珍藏的字样。
用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的话来说,“玫茵堂”珍藏的价值,不在于其是否刷新中国拍卖纪录,而是能对近年来涌入艺术品市场的新买家起到样板作用,可以让他们从来自欧洲的“老收藏”中,体验什么是顶级的中国瓷器珍藏。
苏富比的野心从这里可见一斑,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带给中国市场更多的顶级藏品,而是希望用某种方式引领中国收藏品市场的走向。
仇国仕在许多人面前都反复强调,“玫茵堂”收藏是近30年来苏富比上拍最重要的私人瓷器收藏。
他将重点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就是时间,这是一场经历了50年的长期收藏历史,50年,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就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其二是藏品规模浩大,400件藏品似乎能同某些私人博物馆媲美;其三,仇将其品位搬了出来,美其名曰“欧洲传统老收藏”,至于何谓欧洲传统,又何谓老收藏,仇没有说出个道道来。
唯一能肯定的是,此次拍卖挑选的77件藏品中,明代青花、单色釉等主角;粉彩瓷器大多出自康熙与雍正年代,至于道光和嘉庆年代的藏品,如果不是很特别,也不会被选中。
从“玫茵堂”的角度,其主人不会看不起小件的、价格便宜的作品,而是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他们的收藏中既有一些历朝历代标志性的代表作品,也有一些不是很贵但品质高而又特别的作品。
尽管此次“玫茵堂珍藏”专场拍卖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甚至还有两件藏品是在拍卖后以私人洽购方式成交,但是“玫茵堂”出位了。
两高手三原则
“玫茵堂”的出位,离不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在香港与伦敦从事古董生意的仇炎之与桂斯?艾斯肯纳奇(Giuseppe Eskenazi)。
多年以来,“玫茵堂”主人一直同这两位高人切磋交流,而在仇国仕看来,艾斯肯纳奇帮他具体挑选藏品,而仇炎之则给了这位主人几个终身享用的大原则。
这三十多年以来,艾斯肯纳奇一直是“玫茵堂”主人的“眼线”,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许多明清佳品在纽约、中国香港与伦敦拍场出现,这位“眼线”人物为“玫茵堂”出了不少点子。
而对于仇式三大原则,“玫茵堂”主人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选择珍稀的作品;品质应该最好;完整程度很高。而在具体操作中,这三大原则可以随机应变。就这样,“玫茵堂”主人和仇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仇炎之的收藏主要以瓷器为主,他给“玫茵堂”主人的点拨,或多或少,延续了自己的路子。
曾担任柏林国立博物馆馆长的简?查普曼(JanChapman)在第一次访问私人收藏家的旅程中,去了仇炎之的家。
且查普曼清楚地记得,往后数次重返仇炎之日内瓦之居,细细品味珍藏的情况:犹如步入庙堂,红墙缀金,美轮美奂。客厅置玻璃陈列柜数座,不仅是藏品瑰丽珍奇,就是列展的方法也近乎完美。
“几乎艺术品填满了仇家每一寸空间,”查普曼感叹道,仇炎之之子仇大雄曾回忆道,“每到夜深,父亲未能入眠的时候,总喜欢把陈列柜里的瓷器拿出来重新排置。”
和瓷器说话
在这两大高手中,仇炎之的作用显然更大,以他的经验,不仅授之以鱼,而且授之以渔。因为,他是一个会和中国瓷器说话的人。
仇曾在北平收藏了一只宣德雪花蓝大碗,这只大碗原先为晚清时期一位盐运使所有,后来天津劝业场一家古玩铺以50元的价格买下,北平琉璃厂陶庐斋经理又以500元得到了它。
仇买的时候,价钱已经升到了800元。1980年,香港苏富比仇炎之瓷器拍卖专场中,这只碗卖到了370万港币。
上世纪50年代,仇还曾在香港用1000元港币,买下了一只别人都以为是假货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据赵汝珍著的《古玩指南》记载:“明成化窑斗彩鸡缸杯,现存仅三只。”成化斗彩瓷器,基本上都是官窑产品,在明代已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仇买下的这只鸡缸杯,在1980年在苏富比拍卖时以480万港币落槌,被誉为收藏界“拣漏”的典范。
仇氏生前,曾在1979年将167件藏品卖给上海博物馆。1980年过世后,其家人把他的毕生收藏委托苏富比拍卖,1980年暮春及秋季拍卖其175件藏品。1981年及1984年又分别拍卖其收藏的古玩精品。
而仇炎之作为瓷器藏家的最后辉煌,也留在了苏富比拍卖。
仇走了,却蹦出来一个“玫茵堂”。
- 推荐关键字:藏瓷世家玫茵堂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藏瓷世家玫茵堂的出位传奇
- 2011-04-18
- ·藏瓷世家玫茵堂的出位传奇
- 2011-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