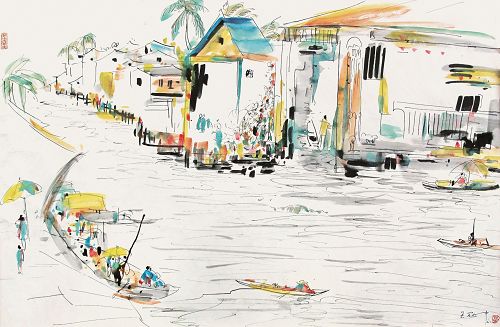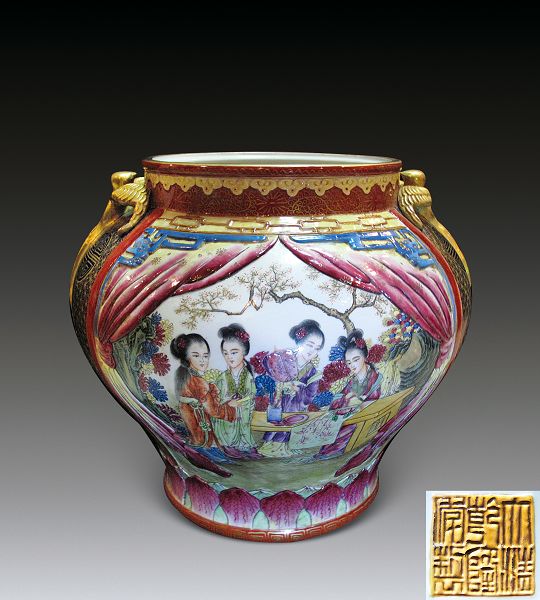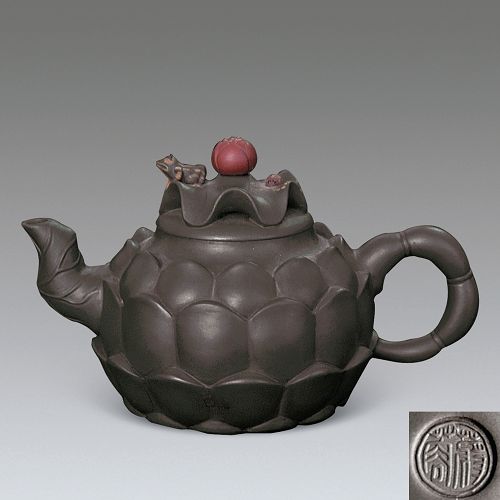现行的教育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把教育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了。我不认为今天能够改变这个局面。这是社会一定阶段的现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难以避免的。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现状,努力改变这个局面。如果现在思想上认识不到这种局面需要改变,那就会延长这个过程。可以提供一些条件,使情况变得更好一些。
开栏案语:伴随高等教育就读人口的增长,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竞争加剧。机会安排、资源配置、质量保证、教育问责、大学分层等问题,成为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必须探索和商议的主题。无论是探索还是商议,都需要有充分的话语表达和思想展开。每一种声音都能够得到尊重并取得抒发的通道,有利于问题的清晰界定和求解路径的多样选择。如是,高等教育问题真正成为所有利益当事人的问题、大众的问题、公共的问题。
为此,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邯郸学院与本报合作,开辟“木铎高等教育访谈”,期望搭建对话和交流平台,倾听不同的声音。
学位不能简单地做成“通用粮票”
记:您对现行的学位制度有什么看法?
李:先简单回顾一下我国学位制度的历史。建国以前,没有一个系统的学位制度,从来没有颁布过正式的博士学位。建国后学苏联,建立过副博士制度,但也没有全面推行。真正建立学位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很短,所以现行的学位制度,有一个逐步发展和建设的过程。应该说至今为止还有和国际上不够接轨的地方。
记:您能具体谈谈哪些方面与国际上不够接轨?
李:比如学位点的评审问题。开始硕士点、博士点和导师要一个个评,后来评各个高校,一个个地评,但每次都会遇到相当多的问题。国际上的做法不一样。比如说可以只评定哪所高校可以设立博士学位,什么科可以设立博士学位,由什么人来带学生,那可以由高校自己来决定。现在这点已经逐渐下放多了,但还是不够。
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李:这是因为国内认为学位是一个,也就是“通用粮票”,全国必须是一样的。实际上同样学位各个学校培养的人恐怕质量未必一致,事实上就是如此。不同的导师指导,不同学校的课程安排,结果肯定不一样。
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差别,北大、清华、北师大是国内名校,这些学校能培养出好的学生,要是培养不出好的学生怎么能是名校呢?当然名校也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好,有些学科就特别好,有些学科就比别的学校要逊色一些。这都是可能的。各校的学生不一样,他们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导师提供的帮助也不一样。
国外都是承认这个差别,名校也会有些学科不很好。好与不好可以由社会去判断,从整体上说,国家只管这个学校是否可以授予学位,或者这个学校某一个大的门类是否可以授予。
记: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个学校可以有自己的标准?
李:当然还是要统一。我个人认为“评”还是必要的,可是要控制。国内有不同类型的学校,有些学校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有些学校以本科为主,不一定都要培养研究生。人们在这方面的观念有些偏差,现在什么学校都争着报学位点。
可在国外就不是这样,我在美国大学教过书,也是名校,这所学校就主要是本科生。这并不影响它的知名度,不一定要和哈佛一样,非要做研究型大学。其实国内真正的研究型大学是非常少的。
高校扩招不能一个模式
记:有人认为研究生可以分成两种,通俗地说做学问和为将来谋职所用的。
李:我不赞成学位有学术和职业的区别,硕士就是硕士,博士就是博士,学位还是应该有统一的标准,水平不能降低。
不客气地说,我认为现在扩招带来了一些弊病。清华到现在也没有扩招,这一点上我很佩服学校,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困难,像文科研究生就招得很少,我在清华今年只招两个研究生,还是分别为两个部门招的,但我觉得这样学生才能够培养好。
当然目前扩招和国情有关,研究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何况国家还在发展中。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最后和世界接轨。
记:正如您所说,扩招和国情有关,那您为什么主张不扩招呢?
李:不是不要扩招。主要看这个学校是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各个学校、各个学科情况不太相同。
现在有那么多的学生要上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多招一些学生这是必要的,我们国家也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基础教育需要拉长时间,要更多的学生来读大学本科。
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些学校强调高精尖的学习研究,不是指应用学科,而是基础学科。虽然大家都知道,没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就是无源之水,发展不了,但是今天基础学科很不容易招到高质量的学生,我最大的意见就在这里。何况真正高精尖的人才不需要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对他们要有高质量的培养。
记:您的意思是,有些高校实行精英教育,其它的则是大众教育?
李:准确地说,是部分高校的部分专业实施精英教育。
现在的很多学科都在转向,学化学的实际上是化工,学数学的实际上是计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学科了,我们需要培养真正基础学科的人才,可是在现在的状态下,这样的人才产生不了。
记:产生不了的根源是现行的大学制度?
李:不在大学,而是在高中。目前的高中教育不能使学生认识科学的重要性,掌握不了学科的方法。
科学本身有其自身的逻辑性、系统性,是演绎和归纳相结合。我们过去高中学数学,所有的课程都是按照学科的逻辑系统编写的。学物理也一样。有人说学这些太枯燥,做那些习题是没有用;还说学这些干什么?其实不能这么实际,这些是基础,就是锻炼人的逻辑系统性和思维方法。
如果学生不具备这种逻辑系统性,那他在科学上很难有发展。文科也是一样,学文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理论上从汉代推到秦,从秦推到战国,从战国推到春秋然后再推到商代,这样才能把中国文字的整个发展搞清楚,它有一个逻辑性,但今天做不到。
学生没有时间广泛学习
记:您在招生的时候对您的学生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李:我希望有一些要求。但是现在的考试制度不能体现这个要求,都是统一出题,我没法有要求。
老实说,多年以来,我对我的学生都不太满意。这不是说学生不好,学生们都很优秀,只不过,他们所学的总是缺少某些方面的东西。我研究的是“古代研究”或者说“古代文明研究”,需要几门学科结合起来,要有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甚至还需要有一定的艺术史等多方面的知识架构,至少这几方面都要有所涉猎,这样的学生才是最理想的。可是今天不可能招到这样的学生,学历史的对考古学不太懂,学古文字的对文献、考古又不太懂,学考古的文献又比较弱。最糟糕的是,他们的外语每每比较差,外国文献很多,非常需要懂外语的人对中外进行比较。
问题出在哪儿?不能怪学生,他们的大学本科学习,没有时间去业余读或者去考虑别的,时间、课程扣得太死,学时太多。我读大学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学期没有几堂课,有很多的时间看书,去图书馆,甲骨文我就是自己这么学的,完全没有导师,都是靠自己。
记:您认为自觉学习是个人原因还是当时的教育体制和方式有关?
李:我先来作个比较,我觉得今天的教育比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降了一个层次,今天的大学好像是那时候的高中,今天的研究生好像是那时候的大学。我读清华就像现在的研究生,上课的学生也就是五六个,有的时候七八个,有的时候就到老师家里去上,这是今天研究生最好的待遇。
现在个别老师带二十几个、甚至三十几个学生,有的连自己的研究生都不太认识。学习上指导不了不说,最大的问题是学生没有机会向导师学习研究方法甚至是做人。我们那个时候跟老师的关系都很好,能从老师的经验里学到很多,而且是通过日常的接触学的。老师是我们的榜样。老师为什么这么成功啊?为什么大家都很佩服他向他学习?我们就看他,读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对学科怎样发展,甚至看他怎么处理各种事务,这就是言传身教。现在的老师连自己的学生都不熟悉,怎么能够言传身教呢?
记:现在的大学教育是不是需要彻底改变?
李:不是这样的,现在教育的优点很多,现在的知识比我们那个时候发展得要深,发展是肯定的。
我所强调的是要加强中学的基础教育。我很明确地反对高中文理分科。一些理科的学生连封信都写不出来,错别字、白字一大堆;学文科的,缺乏科学知识。有好的高中才会有好的大学,高校才能招来好的学生。
记:怎样才是好的高中教育呢?
李:还是比较一下,我读高中期间很有空闲时间,三点多钟就下课,四点是最晚了。下课之后我先到电影院看场电影,然后再回家吃饭。今天的学生行吗?他们每天做功课一直到夜里11点。像我孙子夜里11点钟睡不了觉,第二天早上很早起来,眼睛还是红红的。我很反对这种做法。
好的高中不是说教给学生的知识有多少,而是让他们懂得科学的重要,学会科学思维的方法。以此类推,初中和小学也要办好。但是关键是高中,因为从幼儿园到初中,毕竟还是小孩子,高中是一个人逐渐塑造成型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让他们在人生和科学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到大学后就学该学的基础知识,研究生阶段就能真正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 推荐关键字:李学勤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李学勤表示 我国的考古学还处于起步阶段
- 2006-04-22
-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 2006-04-22
- ·李学勤:功利化是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
- 2006-04-22
- ·李学勤:历史普及要适应大众的需求
- 2006-04-22
- ·李学勤
- 2006-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