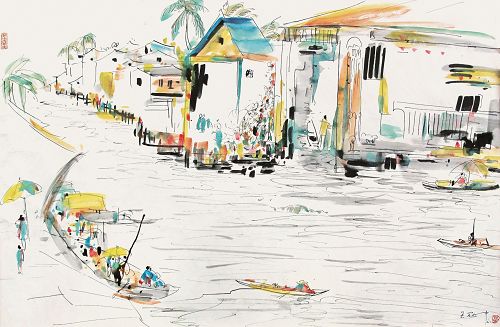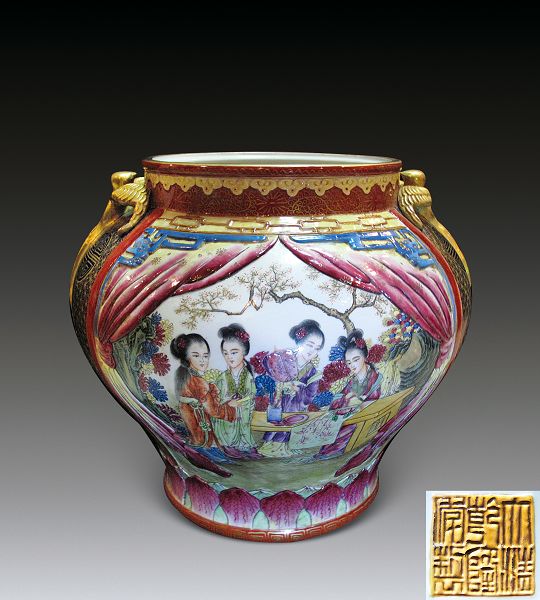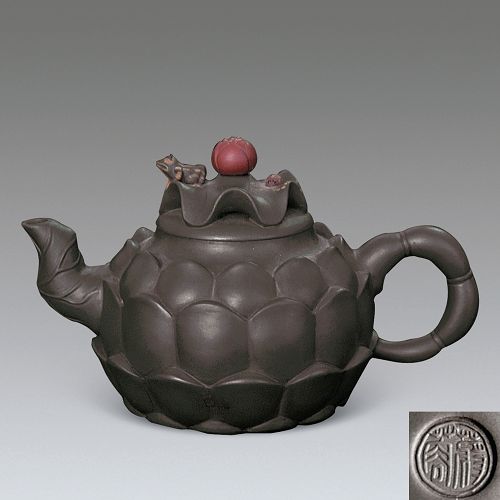某物在未进博物馆、被确定为文物之前,其本身必然有个传递过程,即由生产制造者——销售经营者——拥有使用者——持物者,这个大致传递过程就是流传经过。持物者指的是最后捐献、出售给博物馆的联系人。联系人可能是拥有使用者,或销售经营者;也可能是团体组织,或两者合一。流传经过必须真实可靠,符合每个经手人的情况,特别是要符合拥有使用者的情况。
假冒伪造文物没有真实可靠的传递过程,持物者可能编造胡说,必然出现矛盾和破绽,从而成为我们辨别判断真伪的一个方面。
当遇到一件社会流散文物时,首先要问持物者,此物从何而来,与拥有使用者什么关系,拥有使用者现在的状况如何等。如果是真正的器物,必然讲得合情合理,即使出现一些矛盾,也容易解释清楚。如果是假冒伪造文物,就会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例如“何叔衡用过的钢笔”。1985年纪念何叔衡牺牲50周年,江西一位青年持一枝派克钢笔来京捐献,说是何叔衡牺牲前所用。该钢笔已破旧,美国上世纪30、40年代产品。当问及此笔从何而来时,捐献者一会儿说是他父亲与何叔衡一起工作过,送他父亲的;再问他姓字名谁,从事过什么工作,如何认识何叔衡的,这位青年支支吾吾讲不清楚,又改口说是老师给他的。追问到最后说了实话,他是一名大学生,读到纪念何叔衡的文章,突发异想,在朋友家发现一枝旧钢笔,要过来,编造为何叔衡的,趁放假到北京玩玩,捐献之后可能给报销火车票,但他没想到证集者问得这么详细。
其次遇到一件流散文物时,要由物推断拥有使用者,看有没有使用的基础条件。一些经历简单的器物,持物者说是捡来或者买来的,上面又有明显的标识,就无法继续深问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由器物的某些特点来推断原拥有使用者,一些假冒伪造物也会露馅。
例如“郑振铎读过的《毛选》第四卷”。该郑《毛选》竖排本,已破旧,读过的痕迹很重,封面右下角和扉页上盖有“郑振铎章”印记,持物者说是从旧书店买来的,其他问题不好再问下去。只好再仔细观察该卷,见封底版权页上注明“一九六○年九月第一版”。然后再查郑振铎先生的简历。“1889年生于福建长乐,解放后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7日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1958年郑先生已逝世,不可能看到1960年出版的《毛选》第四卷。再经过与郑先生的印章核查,字体规格出入太大,根本不是郑先生的。为此事又到旧书店查出售者,出售者也叫“郑振铎”,原来是同名同姓。捐献者误认该卷《毛选》为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所有。
再次,按物的流传过程进行追踪调查。在收集文物的过程中,往往遇到没有具体了解人,持物者是单位和部门,拥有使用者是群体,用过之后随意丢弃。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追踪调查,查看每个细节和过程,假冒伪造文物就会露出端倪。
例如“泰兴登城连用过的过桥板”。泰兴登城连确实是英雄连队,战功赫赫。电影、电视、报刊都宣传过。1974年“泰兴登城连用过的过桥板”成为宣传热点,“过桥板”就被当成文物。看到照片便有怀疑,文章介绍说是“门板”,并不像门板。随后找到文章的作者和拍摄者,问询有关情况,他们根本讲不清“门板”的来历。为搞清来源,笔者追踪调查,最后到泰兴县桥头大队才弄清原委。到桥头大队,笔者被大队长带到一个中年妇女家,她过世的公婆曾是支前模范,“过桥板”就是她公婆遗留下来的。在院内真的看到“过桥板”,“过桥板”由三块板组成,长短不齐,薄厚不均,最长240厘米,宽10多厘米,厚3厘米。笔者说,这不是“门板”呀。那个妇女说,哪里是“门板”,是阁楼板。三个月前,部队来拍电影,向她要门板,她家门板已换成玻璃门,随手从阁楼上抽掉三块板钉在一起,就成了“门板”,送回来之后,一人放不上去,就放在院子里。至此“过桥板”真相大白。
- 推荐关键字:文物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千件重庆谈判时期文物邀你免费参观(图)
- 2011-03-28
- ·辛亥革命纪念馆已征得文物6200余件(图)
- 2011-03-28
- ·文物改写历史 明证中国最早发明面条
- 2011-03-28
- ·被掠文物再现拍场 逾2亿法国落槌
- 2011-03-28
- ·江西发现三千年前人类遗址出土的文物(图)
- 2011-03-28
- ·法将拍清朝宫廷珍品 圆明园不赞同买回掠走文物
- 2011-03-25








![民国九年2毫银币[极具收藏增值]拍卖 -中国收藏网](http://image.socang.com/product/2011/03/22/L16445419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