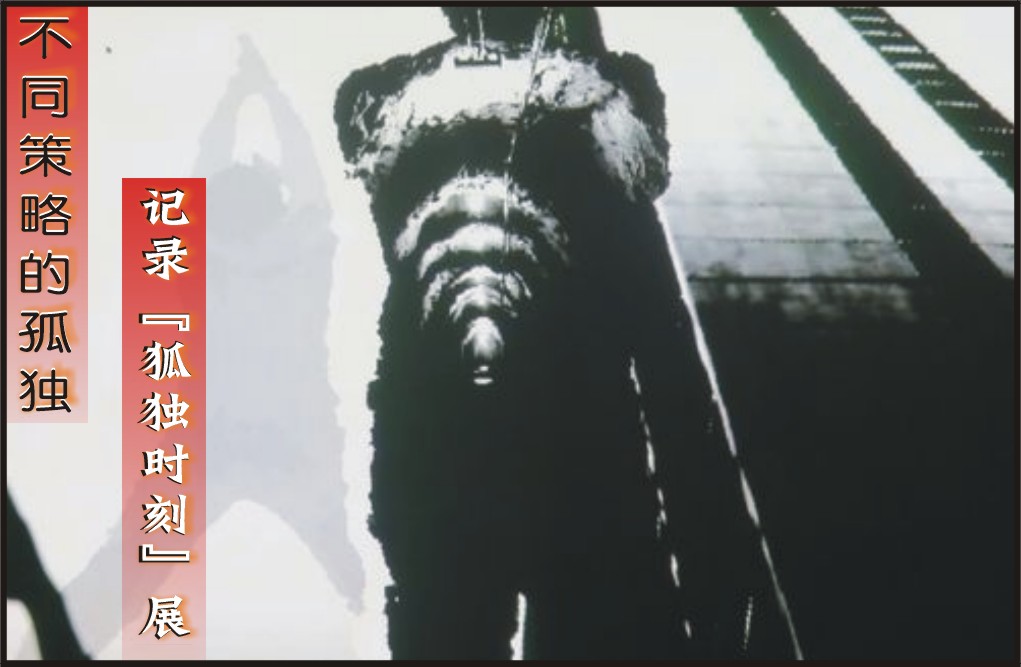艺术“成都”
9月29日开幕的2011成都双年展似乎卯足了劲头要让整个城市都沦陷在这一场烟火欢庆里——早在2011年春节之后的2月28日,双年展团队已经在北京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展览启动新闻发布会,其时除了场馆已经定在成都东郊一个即将被改造为“音乐公园”的老厂房群落之外,一切都还没有定数。对于第一次接手成都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吕澎及其执行团队,这样的动作显示出一种具有野心的进攻姿态,而没有任何谨慎的尝试与防守。从4月14日双年展建筑展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学术讲座,到6月11日双年展首个特别邀请展“看望未来”在文轩美术馆的盛大开幕,再到7月3日的双年展建筑展特别版块“兴城杯”国际高校学生竞赛项目的评选和展示,以及当月12、13日双年展设计展的学术讲座,再到8月份的数场本地媒体通气会,2011成都双年展的相关活动陆续不绝,缓慢而有节奏地为9月底正式开幕的大展造势。
到8月中旬,关于展览的呈现方式基本上尘埃落定,其形式并不像我们最熟悉的国内双年展形式——比如上海双年展,仅以上海美术馆为核心,一个主题展之外有各种外围展星状散开,主次分明。我们所知道的2011成都双年展包含了以下内容:
三个主题展:(一)溪山清远:当代艺术展,策展人吕澎(兼成都双年展总策展人);(二)谋断有道:国际设计展,策展人欧宁;(三)物我之境:国际建筑展,策展人支文军。三个展览不分主次同时开展,展场相近并驾齐驱。
两个配套展:(一)民间艺术展,9月27日在成都市三圣乡许燎源当代艺术馆开幕;(二)精品剧(节)目展演,包含成都市川剧院(陈巧茹艺术工作室)的川剧《马前泼水》、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话剧《霸王歌行》;3、北京普罗之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昆曲《牡丹亭》(皇家粮仓版);河南省豫剧院二团的豫剧《程婴救孤》;四川省川剧院、成都市川剧院、成都市艺术剧院京剧团、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联合演出的《京川折子戏专场》。这两个展览显然定位在普通市民和城市宣传层面,与主题展的当代艺术倾向毫无关联。
此外还有《川流不息:当代艺术文献展》、《记忆缝合》、《日用—常行》等16个由个人或艺术机构申请的特别邀请展在成都各处开幕,开幕时间大多集中在9月29日前后,从9月26日开始到9月30日,平均每天有3个展览热闹开场。
虽然特邀展的数量比不上近两届的上海双年展,但以成都、上海的人口数量和艺术机构数量来比较,显然此次成都双年展的展览数量比例非常高——成都几乎所有艺术机构在双年展期间都有特别邀请展,其中今年7月刚刚开馆的成都当代美术馆加上相邻的那特画廊和尚未启用的相邻建筑就有5个特别邀请展同时展出。
而且2011成都双年展的“特别邀请展”不同于威尼斯双年展、上海双年展的“外围展”,虽然两者都是个人、机构所为,与双年展主题展本身没有关系,但外围展除了展览时间和地域靠近主题展之外,展览的组织和审查机构与双年展完全没有关系,只不过搭了顺风车,方便外地观光客集中观看。而特别邀请展的组织机构隶属于双年展,作品要经过双年展组委会的审查同意,在展览现场有相对统一的双年展LOGO,有些个人申请的展览还可以从组委会办公室获得数万元的活动补贴。这种形式让双年展期间的主要活动——不排除有其它外围展同期展出——具有视觉上的整体性,造成的印象就是在9月29日到10月30日的2011成都双年展展期之内,从东郊到南郊,从市中心到三环外,整个成都市的艺术项目遍地开花。这种盛大的视觉效应显然借鉴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模式,但出发点完全不同——威尼斯双年展的外围展相互独立,气氛自然形成,而2011成都双年展的所有展览都在组织者——成都市政府的控制之下。
成都这座城市的名字来得通俗,流传最广的说法来自宋人乐史的《承平寰宇记》(卷七二):“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另一说不知出自哪里,是“一年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无论确切的说法如何,这里显然描述了一种自然形成聚落的向心趋势。用一种更通俗的方式来类比,此次2011成都双年展可谓真正做到了艺术“成都”——无论开展之后的公众舆论和现场效果如何,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都充斥了艺术作品和艺术行为,汇成一座艺术之城。
当代艺术与城市宣传
由展览组委会发出的“2011成都双年展简介”开头一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2011成都双年展’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组委会具体推进实施,以‘艺术成都 视觉盛宴’为主旨,以‘物色·绵延’为主题,共策划组织有三大主题展、两个配套展以及16个特别邀请展。将在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当代艺术领域进行全面展览,是成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艺术活动,旨在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同时对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进行学术研究与文献总结。展览时间为9月29日至10月30日,主展位于成都市建设南路的成都东区音乐公园和成都工业文明博物馆。”
这里最值得玩味的一个要点是“2011成都双年展”而非“第五届成都双年展”的提法,因为从主办机构到展示内容,今年的成都双年展与往届已经没有丝毫牵系。成都双年展并非始于今年,但由政府直接牵头主办还是第一次。从2001年开始,民营企业老板邓鸿就以一己之力筹办了首届成都双年展“样板——架上”,除2003年邓鸿无暇顾及而空缺一次之外,2005、2007、2009年均如期举办,因邓鸿个人曾学习国画,历届成都双年展也以架上、传统绘画为主。即使在当代艺术价格暴涨的近几年,他的个人趣味依旧主导了展览的主要风格。这也是邓鸿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说“当代”才是主流,但邓鸿以没有任何定语限制的宏大名头“双年展”来做展览,选取的艺术种类却过于单一,如果起初只定名“写实绘画双年展”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这或许也是政府今年将成都双年展“收归国有”重新打造的原因之一。毕竟冠以城市名头的双年展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代表了这座城市对艺术——一种文化形式的认可和推广的标准。
在这里也需要追溯一个已经被大多数人淡忘的展览,举办于1999年12月的“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主办方是仅持续了两年多的中国首家民营美术馆——上河美术馆。作为首家主办——而非赞助——大规模当代艺术展览的民营企业,上河美术馆的这个展览按类型分为书法、国画、油画、雕塑和装置几个部分,种类全面且主题宏大,被称为成都双年展真正意义上的前奏与雏形。(勘误:“世纪之门”是“成都现代艺术馆”举办的开馆展,此馆在2007年拆除。此前由于资料查找的问题,误认为是在陈家刚的“上河美术馆”举办。非常感谢吴鸿老师指出。在此向《艺术与设计》杂志读者及“艺术国际”网站的朋友们致歉。)
因此这一次的成都双年展表面上看是政府的第一次尝试,事实上已经经历过漫长的实验和观察——从1998、1999年上河美术馆对当代艺术大展形式的探索,到2001至2009年四届成都双年展的品牌效应,均已获得虽略有局限但相当正面的效果。
这种类似“招安”的运作方式难免让人联想到关于三十年前“艺术川军”兴起的传说——1978到1979年,四川美院学生程丛林、高小华已经画出《1968年×月×日雪》和《为什么?》等一批“伤痕艺术”代表作,但据说,仅仅是据说,这些学生在校内并未得到认可,这两年内大多数创作的进行都瞒着专业老师和校领导。直到1980年罗中立的《父亲》送展之前,专业老师仍对这些“乱画”的学生嗤之以鼻,包括今天以精湛用色而闻名的画家周春芽,其时的新作《藏族新一代》还被老师们认为“色彩太差”。直到第二年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囊括了展览的大多数奖项,尤其《父亲》捧回大奖,“艺术川军”异军突起,这些学生们一下子成了学校的英雄,嘉奖的嘉奖留校的留校,当时调皮出位的罗中立也在多年之后成了四川美院院长。
但列举此例并无贬义,恰恰相反,这是成都地域性格的有趣之处——无论学院还是政府都不拘于纯粹的意识形态控制论,既然当代艺术风头正健,容易被公众认可,能为主办方带来正面效果,那么政府也可以来办。包括此次聘请的双年展总策展人吕澎——在他写作的艺术史中对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有诸多批评,但在作品方面的判断自有其独到之处。也正因这种宽容度,由政府主导的2011成都双年展目前呈现出来的规模已经直追目前的上海双年展,艺术、设计、建筑三个展览同时开放,受邀参展的艺术家超过150名,国际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新加坡、泰国、丹麦、瑞士、西班牙、加拿大、荷兰、奥地利、比利时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在官方提供的名单中包括“在当代艺术展方面,周春芽、方力钧、张晓刚、何多苓等国内外60多国内外艺术家将参展。在国际建筑展方面,包括米兰世博会总设计师斯特凡诺•博埃里(Stefano Boeri)、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斯塔姆•艾伦(Stam Allen)、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主题馆设计师伊娃•凯斯特罗(Eva Castro)、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设计师EMBT事务所等著名建筑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实验室、南加州建筑学院、中国美院等15家机构参与。在国际设计展方面,邀请到了来自产品、建筑、时装、视觉和新媒体五大设计领域的代表机构以及其他参展人,其中包括纽约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建筑事务所索伊尔(SO-IL),瑞士著名服装、作品及装置设计师团队,香港资深设计师黄炳培、著名影像艺术家邱黯雄、台湾著名建筑师谢英俊等。此外,在特别项目《文学中的建筑》环节中,特别邀请到了享有国际声誉的五位建筑师:张永和、张雷、刘家琨、马岩和王澍”
但是政府的用心显然不完全在艺术的推动和展示本身,在双年展主题“物色·绵延”的阐释中,对成都市新提出的城建口号“世界现代田园都市”进行了着重阐述。以相对自由的艺术形式之名行城市口号宣传之实,看似悖论,在中国却再正常不过。
关于双年展的迷思
但是政府为何如此乐意借助“双年展”的名义并给以如此扶持?意大利一座小城创造了上世纪以来最为瞩目的艺术传奇之一,要知道双年展一词最开始不过是指两年一次的节庆,因为威尼斯双年展的成功,现在“双年展”几乎已经成为艺术大展的代名词,但“节庆”的意义仍然埋在各种艺术双年展的底子下面,与卡塞尔文献展等更加学术和专业的展览区别开来。
所以当“混艺术圈儿”的人们期望在每一座城市、每一年的双年展中试图寻找更加前卫的艺术概念和更新鲜有力的艺术形式时,政府等承办部门看到的却是双年展的“大”和热闹,动辄包含整座城市的文化意义,在形式上没有边界,没有严格限制——除了“两年一次”这一死规定之外,双年展可以有固定场馆也可以没有,可以设立国家馆也可以不设,可以有主题大展也可以只以博览会的形式出现……此次2011成都双年展艺术、设计、建筑三个主题展并行的方式在国内尚属首例,但叠加效果相当有趣,很可能成为其他城市展会的模仿对象。而特别邀请展形式的采用,对政府来说增加了控制力度,可以视为艺术家对现实世界的和解与折中,圈里圈外各有所得。
但也因为这种开放与折中,依靠“双年展”来提出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者依赖双年展去推动艺术进展的愿景已经越来越无法达成,相反,中国艺术家也逐渐开始看重个案研究式的文献展览,而不仅仅满足于展示和吸引观众的双年展。寂寥的实验与盛大的集会共生,双年展回归其位,意识形态与自由创作之间的悖论或许才会逐渐达到平衡。
- 推荐关键字:成都双年展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艺术社区合作模式亟待创新(图)
- 2011-11-16
- ·易英:中国元素压倒中国现实(图)
- 2011-11-16
- ·2011成都双年展圆满落幕 艺术的味道绵延
- 2011-11-07
- ·2011成都双年展6日正式闭馆
- 2011-11-07
- ·在城市与建筑中 引进“时间”的因素
- 2011-10-28
- ·成都双年展延期至11月6日
- 2011-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