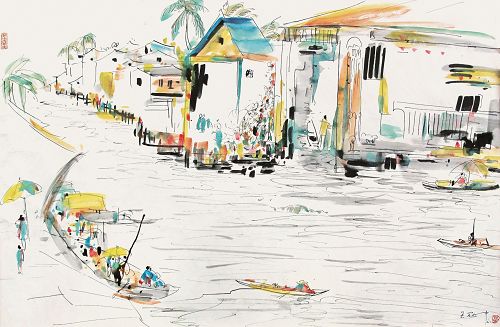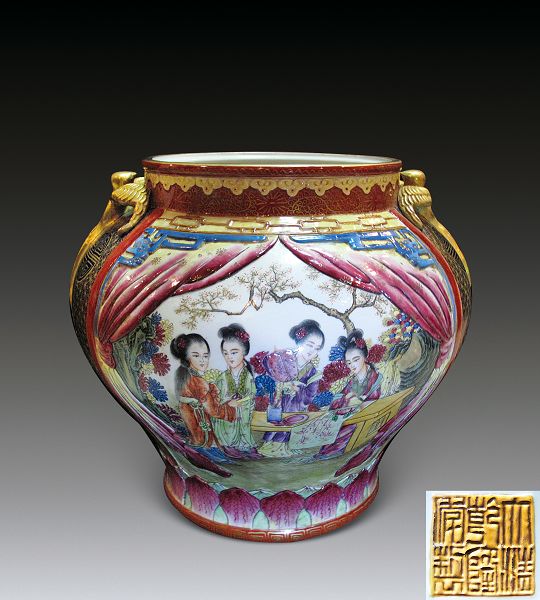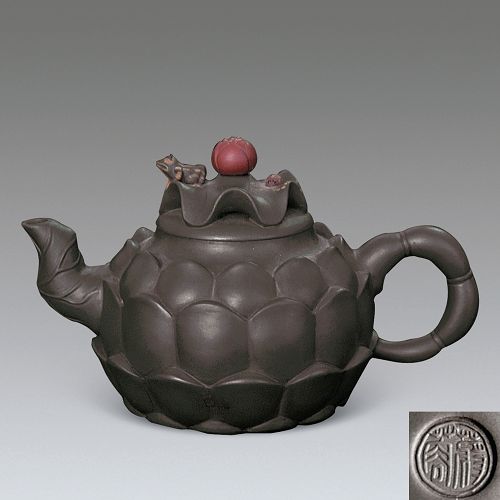华池路,离上海地铁7号线岚皋路站不远,内环近中环的好地。华池路211弄的铁路新村,是上海的老式棚户区,老上海人和来上海打拼的外地人杂居于此。用红漆手工刷出的 “加工棉花胎”招牌悬在弄堂进口,日用杂货铺、裁缝铺三三两两,晾晒的衣服在空中摇曳。近40度的高温下,这里的空气闷热,租客们说, “房源可紧俏,因为算是市中心,每年都得抢着订。”
老弄堂是繁华都市生活的另一部分,并不算稀奇,只是那斑驳的旧墙上,猛地跑出色彩斑斓而艳丽的涂鸦画作——布满整墙的长发如瀑布的厚嘴唇女人、抽象的龙凤图,甚至是 “戴防毒面具的大象”,瞬间抓了人的眼,让这条略显沉闷的弄堂在阳光下活跃起来。
在这里住了一年多的河南大姐,午间在拥挤的房屋里拿木盆和搓衣板洗衣服。租屋外部一根下水管的上方,巧妙地画上了一个坐在澡盆里洗澡的胖娃娃,让人感觉澡盆里的水正顺着下水管哗哗流着。大姐清楚地记得, 5月份,是德国人来这里画了画,而且知道这些德国人是上海世博会德国馆请来的。 “那天有个人从三四点开始画,涂涂喷喷好半天,一直画到天黑,后来我还拿了家里的台灯照着他画。”德国人走前,送给大姐一本画册,是德文的,铜版纸质量很好,如今已经被她贴在玻璃窗上当 “窗帘”,但她指着上面的德国人头像说: “看,就是这个人画了对面墙上的那个女人。”
大姐喜欢这个画,她觉得漂亮好玩,她的11岁儿子和3岁女儿也很喜欢。 3岁的女儿胖胖的,总在墙上的澡盆旁边玩水,也常常被慕“涂鸦”名而来的摄影师拍到景里。但和大姐一样在弄堂里做裁缝的另一个大姐则不喜欢,“人要小小的才好看,‘小样’‘小样’,小了才有样子。 ”她对这幅棕色皮肤的长发女人很不满,也觉得“大象”的比例很不协调,“画画总是要有目的的吧,要想好画成什么样子才画,也不知道这些画画的人想干吗。 ”一度居委会还差点以市容环卫条例为依据,要拿石灰把画抹去,还是居民想办法争取,才得以保留。
德国艺术家并没有想到他们5月份的一个偶然行为,竟然成为了一个事件,并被一直讨论至今。
8月份,这群艺术家再一次来到上海,“华池路涂鸦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马可罗和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的新闻官孔然蒂一起坐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罗眼睛碧蓝而清澈见底,他是德国嘻哈基地成员,同时也是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的城市艺术项目团队成员。
没有刻意选择,也确实如裁缝大姐所说,没有目的。孔然蒂则说这就是 “偶然”——因为德国馆要装饰位于红坊创意区的一个老厂房,于是请来了德国涂鸦艺术家;在老厂房涂鸦完工后,还剩下了很多颜料和素材。艺术家们觉得在上海得到了很好的招待,上海的人们都很友好,也应该有所回报。于是在中国朋友的牵线下,他们来到华池路的一个涂鸦学校“涂鸦公园”内作画,此后又给居民画画。
马可罗说,当时找了翻译,和部分居民进行了沟通,艺术家们会问问居民想画什么,比如有个妇女说要画鸟儿,他们就画了鸟,还有很多居民就是看看热闹。前后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他们装饰了几乎所有可装饰的墙。“这就是给居民的礼物。我们没有特意去考察华池路的环境,这就是一种缘分,我们来了,我们画了,希望能够给居民们带去色彩和欢乐。 ”
“我们从社会获取,我们又回报社会。 ”马可罗说,这就是嘻哈(HIP-HOP)艺术的主旨。
“涂鸦”是嘻哈的主要要素之一,其他的嘻哈要素还包括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街舞、音乐、服饰乃至刺青。马可罗说嘻哈可以把各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可以把各国的艺术家都聚集在一起进行创作,这是超越语言、超越国籍和种族的艺术。如今的嘻哈艺术早已不是一些人理解的街头文化,一些大公司的知名品牌也会指定用“涂鸦”来为自己的品牌做宣传。
而这更是一种交流方式。现在在世博园区德国馆外,每天都有涂鸦艺术家为参观者提供涂鸦服务,可以喷涂在雨伞上,可以喷涂在帽子上。孔然蒂说,这正是以“和谐都市”为名的德国馆的精神体现,让各种文化能够交流和共融。
3个月过去了,华池路211弄墙面上的画作仍然如新,有意思的是,贴“办证”一类“牛皮癣”的人似乎也刻意避开了画。有工人送货经过,会指指点点,探讨一下“大象”为什么要戴面具。这里吸引了很多人来拍照,乃至记者来采访,据说前前后后有两三百号人。曾经有居民对着摄影者发问:“你们为什么只关注这些涂鸦,而不去拍拍我们这里简陋的生活? ”
华池路的生活本质上没有因为涂鸦而有所改变。
河南的大姐一个月要为四个人居住的10来平米棚户区付600元的租金,正在犯愁自己的三岁女儿因为外地户口不能上幼儿园,在铁路新村住了60年的陈大伯对环境有诸多不满,杂货店的老板也总还是在午间时分躺在躺椅上打瞌睡……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嘻哈文化,不知道德国人为什么来涂鸦,对画好不好看也各有各的看法,只是这个弄堂的生活因为这些涂鸦多了色彩,多了谈资,也多了想象空间。
- 推荐关键字:涂鸦 弄堂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艺术家因涂鸦被捕 班克斯挺力相助
- 2011-03-11
- ·英涂鸦艺术家成奥斯卡“神秘人”(图)
- 2011-02-22
- ·英国涂鸦大师班克斯涂鸦作品现身美国(图)
- 2011-02-18
- ·英国王子被艺术家涂鸦(图)
- 2011-02-14
- ·涂鸦,都市“异”彩(图)
- 2011-02-14
- ·休斯顿计划五年消灭城市涂鸦(图)
- 2011-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