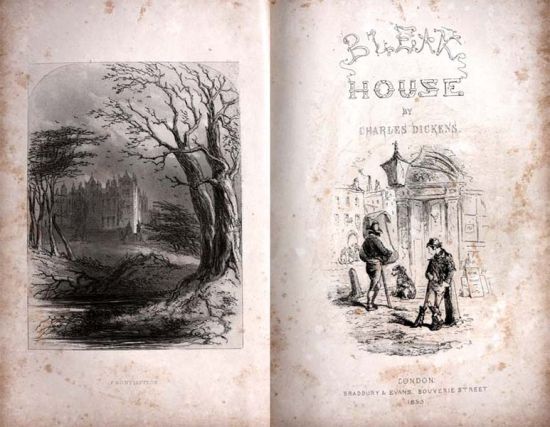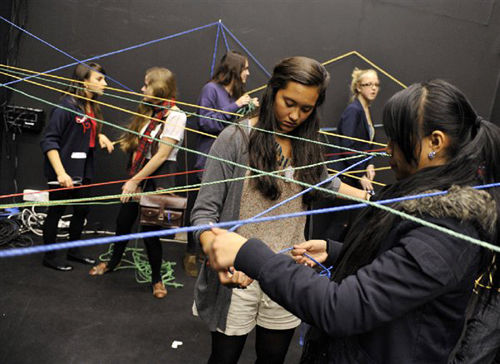巴巴德·葛西里《内战》,2005 (阿兰画廊提供)
尽管处于孤绝状态,伊朗的当代艺术界非常活跃,充满创造力,却依然鲜为人知。ARTINFO所在的路易斯·布罗恩媒体公司(Louise Blouin Media)旗下刊物《Art+Auction》的主编本杰明·吉诺齐奥(Ben Genocchio)最近进行了一场伊朗之旅,为我们带来特别而稀见的报道。
我在德黑兰,这个国家的悖谬甚至在著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中也明显可见。这座博物馆由伊朗艺术家、建筑师卡姆兰·迪巴(Kamran Diba)设计,作为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著名的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建筑的颠倒版本,环形中央坡道盘旋而下,这座建筑最初给人的感觉是欢迎游客并保养良好。在我头顶上方,中央大厅悬挂着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动态雕塑,是为该馆1977年开馆专门购进的,两年后,伊斯兰革命爆发,结束了君主奢侈放纵的统治。在我右侧是一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1966年的无题雕塑作品,镀锌铁制部件从地面至天花板竖直地排成一排。目前看来还算不错。
贾德这件作品如今大概价值500万美元,只是为这家机构创建而购买的数百件印象派及现、当代艺术作品中的一件,2007年伦敦《卫报》的一篇文章称这批作品的价值大概近于25亿英镑。这件作品和考尔德的作品属于仍然在展示中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西方作品,其余的莫奈、凡·高、毕沙罗、雷诺阿、高更、图卢兹-劳特累克、马格利特、米罗、勃拉克、波洛克和许多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便埋没在仓库中不见天日。仔细查看一下贾德的雕塑作品,我发现9个部分中有几个部分带有划痕,其中之一的划痕非常严重,通过某种溶剂的清洗又令其变色。它们在墙上的布置也不平衡,并且固定得很糟糕——有些是歪斜的。
无须特别深入地观察,便可发现近年来伊朗社会遭受的破坏。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言之成理或感觉正常。平常百姓的生活浑浑噩噩、怪异、错乱、充满意外、杂乱无章,我从机场乘坐的的士在路边被穿制服的警察拦下,强行在路边检查我的包。在革命之前,伊朗乃是该地区最为文明的、最称得上世界主义的国家之一。一场进步运动发生在其艺术与文学领域,电影与电视产业也发展成熟。(如今该国在广播电视业的垄断已将后者全然扼杀。)伊朗同时也曾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社会。什叶派穆斯林占其大部分人口,他们虔诚却并不狂热。现代化与穆斯林曾在伊朗相处融洽。
“革命前我们公开地饮酒,私下里祈祷,而如今我们公开地祈祷,私下里饮酒,”我的向导如是说,他是一个有着工科学位的聪明人,他的工作是陪我到所有地方并报告我的一切活动。对此他直言不讳。有他在我身边,便是我进入这个外国人极度不受欢迎的国家遭遇的现实情况。根据伊朗官方报告,该国每年接纳游客约1万人,与该国诸多的文化魅力相比,这个数字真是低得惊人。阿契美尼德帝国(约公元前550至公元前330年)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便是该地区最伟大的考古遗迹之一。与此相比,在迪拜附近一家华丽的购物中心伴有机场和艺博会,每年的游客量都能达到约100万人。
我的向导与我建立了友谊,他承认他正试图举家移民。他已申请过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公民身份。他并不是特例。我在德黑兰艺术圈中见到的许多人也都在寻找着出逃的途径。这不单是由于该国政府的核野心受到的国际制裁对经济与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已令年度食物和燃料补贴缩减了逾1000亿美元(此前这些都由伊朗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收益免费提供),也不单是由于对反对派绿色革命的持续镇压——人们说,这些,他们都能忍。实际的原因用美籍伊朗喜剧演员康比兹·胡赛尼(Kambiz Hosseini)的话来说,是“希望的灭绝”。2009年夏天的选举出现严重争议,反对派的支持者们首次走上街头,随后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和封锁工事,令人们确信一切都不会发生改变。从此政权与广大人民分得越来越远。其分歧明显可见。
我的访问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是面对在伊朗发生的人类悲剧。无论伊斯兰革命在当时是何等的合理,如今却是蓄意地、有系统地破坏着该国人民的愿望和机遇,特别是对该国的年轻人们而言。工作机会极少或根本没有,也几乎剩不下一点进取精神,因为人们知道,统治精英掌控着一切。社会深度腐败——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皆是如此。坦率地说,这是个耻辱。这还令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然而还要更糟糕,因为在如今的伊朗,所有文化的东西都是政治的。独裁政府甚至试图对发型实行管控,其中只有9种发型是官方“推荐”的。
一些出国访问的伊朗艺术家决定留在国外。2009年春天,拉明和罗科尼·哈埃里扎达兄弟(Ramin and Rokni Haerizadeh)在巴黎达太·罗帕克画廊(Galerie Thaddaeus Ropac)举办他们的首个展览后回国的途中,据《W》杂志2010年12月号报道:“他们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诫他们不要回国。”他们的作品在对一位德黑兰藏家房屋的突袭式搜查中被没收,恐怕他们回国后也会被逮捕。兄弟二人申请居留阿联酋,如今生活在迪拜。尚不知能否、何时能够安全回国。处处弥漫着焦虑。
然而,尽管政府将恐怖施于国民,日常生活看上去还是井井有条。走在街上你不会感到像在巴基斯坦那样提心吊胆。伊朗是个有秩序的社会——保守,是的,但并非在传统上令人无法忍受或明显使人感到压抑。在大街上你不时会看到年轻女子感到厌烦不已,由于没有正确佩戴头巾或面纱,或是化妆过浓而被人(通常是年长者)指责。但女人可以开车、吸烟、独自坐在公园中或咖啡馆里。这里不是沙特阿拉伯。这里还有许多公共剧院、博物馆、画廊,以及公共和私人艺术学校。根据非官方数据,伊朗每年的艺术学校毕业生数量达到4万人,其中包括平面艺术家。文化在这里受到重视,却也怀着恐惧:许多艺术家、编辑、作家和电影人被囚在狱中。
据伊朗新生独立当代艺术杂志《明日艺术(Art Tomorrow)》主编哈米德·凯什米谢坎(Hamid Keshmirshekan)称,德黑兰以其画廊为荣,私人画廊有60余家——如果将公共空间计算在内,则有100余家——散布在城市各处,但大多聚集在较为富裕的北部市郊。其中(如果有的话)极少有专为作为画廊而建造的,而是许多位于私宅中,因此这幅图景令人感觉颇为特别。有一小部分个人支持艺术。像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大多数画廊主是女性;同样,像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展览一般只持续两周。
我在德黑兰时踏访了约12家画廊,见了许多有才能的艺术家,并看到许多大胆而进步的作品。好消息是伊朗艺术依然存在并且表现良好。坏消息是这些作品中有许多无法公开展示,或只能在开幕式上展示几个小时,随后便被从墙上摘下投入仓库。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门对什么能展、什么不能展有相当严格的控制,我见过的所有画廊主都有被请去该部门、被要求解释并在随后移除墙上的作品的经历。具有挑衅性和渎神性的作品会令商家和创作者都受到指控。
年轻艺术家尤为大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畏惧他们面对的危险,却也因为他们对生活在与他们无关的革命的后果中感到尤为失意。其中许多人在作品中以幽默为武器,委婉地嘲弄毛拉集团的统治,或是指出伊朗当代生活的荒诞和矛盾。甚至连本地人都似乎不能理解统治他们社会的逻辑,或许没有人理解:在我到访之前,几尊大型的、突出的公共雕像在夜晚从基座上神秘失踪,再也没有现身。看到这些年轻人将艺术创作奉为一种抗议的模式,令人当即感到鼓舞却也不安。他们已发现体系的裂缝,并准备将其翻个底儿朝天。
然而在该国占据主导的氛围是黑暗而紧张的。待在这里很不开心。人人自危——在最近席卷中东的起义浪潮之后或许尤其如此。毫无疑问,当局在街道上和互联网上都予以镇压。今年2月,伊朗的互联网服务曾被停过一段时间,我在德黑兰的一位朋友随后报告了拨打国际长途电话的困难。持改革观点的媒体人和政治家被拘。在伊朗,国家的镇压明显加剧。那里的社会处于一种《经济学家》的一位记者称之为“被精心策划的全国紧急状态感”之中。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当代伊朗艺术家们渴望自由。然而外人却并不总能理解他们表达的不满。比如今年4月,几家德黑兰的重要画廊联合举办了一场70位艺术家以花儿的意象创作的艺术作品联展。是的,花儿。这场展览是与31岁的摄影师梅赫拉奈赫·阿塔西(Mehraneh Atashi)团结一致的表现,这位摄影师因拍摄德黑兰街头抗议而在2010年1月被拘,而后被释放,条件是她得开始拍一些更加“合宜”的照片,比如当地美丽的花儿。
摄影在这里确实作为一种独特的触及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手段而出现。伊朗摄影师们开始转向纪实摄影。西丽·阿里阿巴蒂(Shirin Aliabadi)和莎蒂·嘉德里安(Shadi Ghadirian)因探讨伊朗社会中的女性问题而闻名。两位都在国外举办过展览,她们的作品也都位居欧美美术馆的藏品之列。嘉德里安与几位朋友最近一起建立了180余位伊朗摄影师的网站fanoosphoto.com,举办艺术家们的在线展览,并公开纪实摄影师们的联系方式。网站对该国当下创作中的作品的选择颇具见地。偶尔会有藏家买下一幅照片,然而在伊朗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摄影市场。
住在德黑兰的纪实摄影师阿巴斯·库萨利(Abbas Kowsari)和纽莎·塔瓦库里安(Newsha Tavakolian)在国外展览和销售作品取得了一些成功。库萨利喜欢描绘伊朗社会的荒诞,他拍摄的身穿黑色罩袍的女子警校学员沿绳索从公共建筑物的一面下降的照片如今名声在外。此外还有阿拉什·法耶兹(Arash Fayez),前途无量的年轻摄影师,今年只有27岁,在上一届巴黎摄影博览会上获得了一些关注。在最近的“记忆的衰落(Decadence of Memories)”系列作品中,他用宝丽来照片拍摄了5件最爱的童年纪念物(包括一个球和一个熊形调味瓶),以德黑兰破碎的城市景观为背景,召唤童年时代的褪色梦幻。一切在这里都快速地消失,包括梦幻。
是娜孜拉·诺巴莎莉(Nazila Noebashari)向我介绍的法耶兹,她是一位藏家,两年前开了阿兰画廊(Aaran gallery)。这是一个紧凑却令人愉快的错层式空间,在德黑兰市中心一幢家庭建筑的二楼,可以俯瞰被树木环绕的庭院。艺术作品倚墙而立,靠在临时的画架上,或与成堆的画册和书籍一同放在地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看到玛亚姆·阿米尼(Maryam Amini)和哈迪·纳斯里(Hadi Nasiri)的照片,然而很抱歉,(由于诺巴莎莉的请求)我不能描述这些作品,恐怕这会给艺术家和画廊主带来麻烦。诺巴莎莉最近在美国洛杉矶的18街艺术中心(18th Street Art Center)组织了一场伊朗艺术家群展,她很勇敢,却并非一味蛮干,这是她的原话。
这家画廊主要展示年轻的、实验的艺术才俊的作品,也是德黑兰为数不多的以艺术家为本而不是以赚钱为本的画廊之一。2008年迪拜邦瀚斯(Bonhams)拍卖会上,德黑兰画家法哈德·莫西里(Farhad Moshiri)波普风格的画作《爱(Eshgh)》(丙烯、施华洛世奇水晶、亮粉)以104.8万美元成交,这令越来越多的画廊致力投资那颇感壮大的伊朗艺术品市场。而生活在德黑兰的重要当代艺术家,包括莫西里,拒绝与那些暴发户们合作办展,他们说这些人缺乏专业性。他们也担心会被那些商家和无耻的投机者们利用。
年轻艺术家中另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是行为艺术。德黑兰最前卫的画廊阿扎德(Azad)是此类作品常常上演之处,这家画廊位于一个宁静的住宅区中,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的地下室空间,有着涂成黑色的墙面和混凝土地板。我在这里见到了37岁的观念艺术家埃米尔·穆贝德(Amir Mobed),此人在阿扎德做过一件相当惊人的行为艺术作品,并因此而出名。这件作品受克里斯·博登(Chris Burden)的启发,穆贝德站在一个靶子前,身穿紧身衣裤,以一个铁盒护住头部,请画廊的游客们用气枪向他射击。他说,这是一次象征性的死刑,带有与言论自由相关的信息,以及艺术家所属的沉默的一代人的心愿。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穆贝德的作品只是我访问德黑兰期间看到或听说的与伤痛、毁灭和暴力有关的几件作品中的一件。在过去的2009年,同样也是在阿扎德,奈达·拉扎维普尔(Neda Razavipour)创作了名为《自助(Self Service)》的偶发艺术作品,她邀请画廊的游客们用剪刀破坏一块波斯地毯,第一天结束时便已全部毁掉。而后是西丽·法克西姆(Shirin Fakhim)持续创作的幽默却令人不安的现成品雕塑作品《德黑兰妓女(Tehran Prostitutes)》,涉及这座城市中“性工作女郎们”的生活,其中许多人是被家庭暴力和性侵犯所迫而从事这种交易的,依照该国严酷的宗教法规,从事这种交易是要判死刑的。
我看过的大多数最好的艺术作品都包含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谨慎隐喻。在该国崭露头角的艺术新秀中,著名伊朗作家胡桑·葛西里(Houshang Golshiri)之子、29岁的巴巴德·葛西里(Barbad Golshiri)是新生代艺术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2005年强有力的明信片尺寸摄影作品“内战(Civil War)”将德黑兰各处的政治、宗教和商业广告牌作为对伊朗社会核心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毫不隐晦的隐喻。许多广告牌虚张声势、流于宣传,却在作品中被重塑,颠覆了原有的信息。
在丝绸之路画廊(Silk Road Gallery)的一次经历或许最能概括当今伊朗艺术家的尴尬地位。丝绸之路画廊是一家私人画廊,在城市北部的一幢公寓大楼中,专攻伊朗摄影作品。在认真地欣赏过艺术家和获奖作家佩曼·胡斯曼扎达(Peyman Hooshmandzadeh)(他的书刚刚被禁)的一组摄影作品时,一幅照片使我停下脚步,照片展现的是一家德黑兰的咖啡馆中,年轻人们通过书籍观看伊朗著名的旅居海外的当代艺术家西丽·娜沙特(Shirin Neshat)的摄影作品。我问画廊主阿娜希塔·葛贝安-艾泰哈迪(Anahita Ghabaian-Ettehadieh)她们为何对娜沙特的作品感兴趣。“因为在她自己的国家从未展览过,”她如是回答。(申舶良/译)
- 推荐关键字:艺术现状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2011 Art Basel最佳展位盘点(图)
- 2011-06-17
- ·当代艺术现状:精神虚无批量生产
- 2011-06-13
- ·当代艺术现状:精神虚无批量生产
- 2011-06-03
- ·威尼斯双年展开幕 王小松装置作品创新纪录(图)
- 2011-06-02
- ·威尼斯双年展开幕 王小松装置作品创新纪录(图)
- 2011-06-02
-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6月1日正式实施
- 2011-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