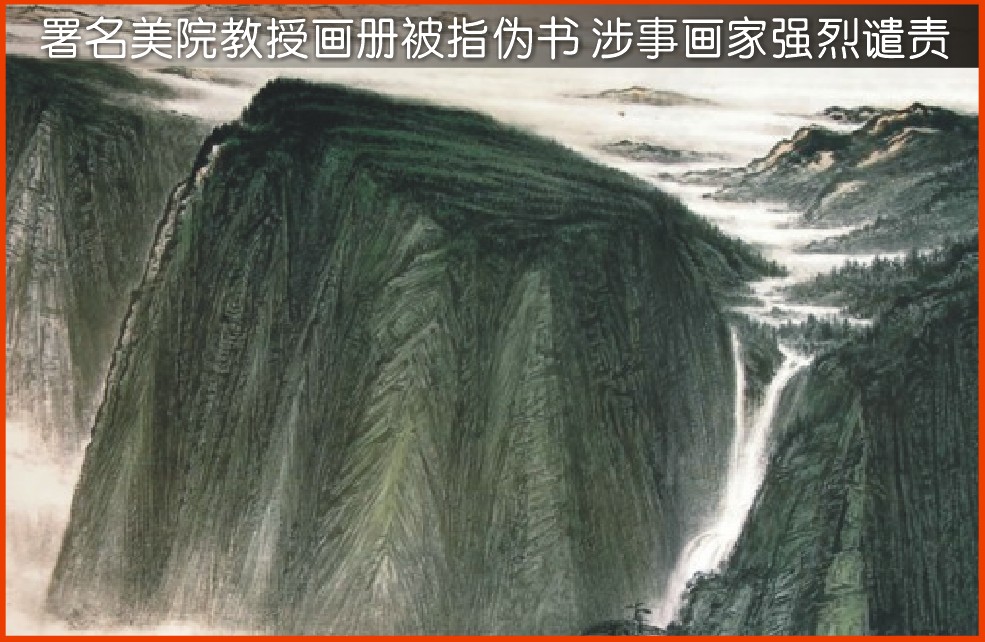弗里达·卡洛作品《两个弗里达》(1939)
一场集中展示弗里达等北美女性艺术家作品的展览“奇境记:美国和墨西哥的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正在洛杉矶州立美术馆展出。该展览也是首次大规模对北美女性超现实主义画家进行考察。展览标题直接来源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每个女性心中都有一个爱丽丝。”策展人说,“有些人把自己画成了爱丽丝,她们相信做一个有创造力的女人就意味着要有一些怪异。”
很多人知道弗里达·卡洛。这位命运多舛的墨西哥艺术家、画家迭戈·里维拉的妻子,因她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而享誉世界。但她只是20世纪众多女性艺术家中的一员——她们或许曾经只是男性艺术家的妻子和情人,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她们的价值逐渐得到了肯定。近日,一场集中展示这批女性艺术家作品的展览在美国拉开帷幕——1月29日至5月6日,洛杉矶州立美术馆展出“奇境记:美国和墨西哥的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该展览由洛杉矶州立美术馆和墨西哥现代美术馆携手举办,也是首次大规模对北美女性超现实主义画家进行考察。
本次展览的展品涵盖绘画、雕塑、摄影、视频等不同媒介,共175件,出自47位艺术家之手,时间跨度长达50年,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这段历史时期的末尾,超现实主义更与女性主义运动重叠,并互相影响。其中,路易斯·布尔乔亚、利奥诺拉·卡灵顿(Leonora Carrington)、弗里达·卡洛、李·米勒(Lee Miller)、多萝西亚·谈宁(Dorothea Tanning)和雷米迪斯·瓦罗(Remedios Varo)等都是两大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一些女性不喜欢这样以性别的形式被单列出来,但你不得不从群体中挑选出那些易被忽略者,这样她们才有机会被平等对待。”联合策展人伊勒妮·福特(llene Fort)表示。继2009年曼彻斯特艺廊举办“无政府的天使:女性艺术家和超现实主义”,梳理过欧洲的女性艺术家之后,本次展览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美国和墨西哥。
本次展览由洛杉矶州立美术馆的福特和墨西哥的泰勒·阿珂(Tere Arcq)共同策展。在洛杉矶展出之后,在今年晚些时候巡回到魁北克和墨西哥。
弗里达和朋友们
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也许是萨尔瓦多·达利1931年那幅怪怪的小油画《记忆的永恒》。画面中,软塌塌耷拉着的怀表在荒凉的土地上散落开来,营造出一种过目难忘的关于时空之柔韧性的意象。在洛杉矶州立美术馆,类似的主题被再次唤醒,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超现实主义的永恒”。
两次大战之间,超现实主义在欧洲掀起了小小高潮,它对于心灵和文化的探索主导了巴黎的学院。它曾经恰到好处地呈现了两次灾难性大战间那混乱年岁中现代生活面临的迷惑和压力,它以一种非逻辑的图景表达出原本理性的欧洲社会在冷酷混战中的无助状态。而这股高潮似乎只是昙花一现。二战之后,抽象表现主义、新达达主义、波普艺术、极简主义等其他形式纷至沓来。超现实主义仿佛已被大批搬进了博物馆——历史的收藏室。
然而,一切并非到此为止。在本次展览的175件作品中,有近40件创作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超现实主义大主教”安德烈·布雷东正忙于散布教义、提供祈福、互通有无。布雷东曾经的妻子杰奎琳·兰巴(Jacqueline Lamba)也位列参展的47位艺术家之中。在展出的全部作品之中,有超过1/4的作品创作于1950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奇境记”延续了超现实主义的童话。而它们的缔造者,也正是这个展览的另一个关键词——女性。
1927年,布雷东第二篇超现实主义宣言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性别观点。他将女性看做艺术家的缪斯,男性艺术家从女性的特质中汲取创造力的养料。“女人的问题是最不可思议和令人不安的。”布雷东曾经表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有一句名言,“女人到底要什么?”布雷东想当然认为女人只想要永远被置于“他者”的位置上。
而展厅里的作品直截了当地回应了“大主教”的论点。弗里达著名的1939年《两个弗里达》紧挨着鲜为人知的海伦·路德伯格(Helen Lundeberg)的作品《当时艺术家的双重肖像》(1935)。
“弗里达和海伦经常会画到相似主题,海伦总是早先一步。我不认为她们互相认识,但是作为一名富有创造力的美丽女性,她们一定有很多相似的感受。”福特说,“事实上,这些女性90%都具有美丽的外表。她们的美丽、她们的天赋、她们的复杂内心,赋予她们力量进入这个世界……作为爱人和缪斯,这是男性艺术家看待她们的方式。但是女人希望做自己的艺术。”
新的大陆,梦的土壤
新大陆没有欧洲诸多传统的束缚,在美国和墨西哥等欧洲流亡者聚集的地方,当男性艺术家将女性作为自己欢愉的投射对象,女性超现实主义画家从自身的潜意识和梦境中寻找非凡的视觉意象。对于女性超现实主义者而言,不论是本地人、流亡者或暂时的访客,北美的土地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重塑自我和充分表达的机会,她们探索的角度关于身份:肖像、双重肖像、自我指涉的图像,这些都成为她们心灵旅程的展示或伪装。
“在很多方面,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和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相似。她们的创造力常常被抑制或边缘化,在这个似乎有些奇诡的世界中,逻辑似乎派不上用场,”策展人、美术馆美国艺术部门负责人福特指出,“北美为她们提供了在欧洲享受不到的独立环境,她们有机会改造这片土地,将之布置为她们的仙境。”
因此,本次展览标题直接来源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每个女性心中都有一个爱丽丝。”福特说,“有些人把自己画成了爱丽丝,她们相信做一个有创造力的女人就意味着要有一些怪异。”
在展出作品中,一些画作明显呈现出和爱丽丝的联系,例如,1943年西尔维娅·费因(Sylvia Fein)的《茶会》。画面中,艺术家将自己画成爱丽丝的样子,茶会上没有其他客人,桌上摆放着梨和石榴。当时,艺术家的丈夫正在二战中服役,费因创作了这幅画来表达她内心的担忧和孤独。
在展览的引子部分,最说明问题的作品是多萝西亚·谈宁的《生日》(1942),在这幅超现实的自画像上,艺术家身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长裙衬衫,柔弱的身体站在迷宫入口。她像一位迷人美丽的女巫,身边匍匐着某种神秘的生物,据说闻到它毒液的气味就能致人死命,而女巫本人似乎也能够以眼神一瞥达到同样效果。《生日》代表着一股觉醒的力量,同样也暗示着展览的主题。“奇境记”呈现的,不是灰尘铺满的欧洲,新大陆昭示着重生的希望。对于超现实主义女画家而言,提供了尤为丰富的艺术可能性。
弗里达·卡洛的双重自画像回溯了她的德国和墨西哥祖先——一位欧洲妇女和一位土著妇女执手相牵。她还画了一幅传统墨西哥婚礼的肖像,当时她和丈夫迭戈·里维拉的婚姻面临终结,而她以画笔起誓嫁给自己。
雷米迪斯·瓦罗也许是展览中继卡洛之后第二重要的角色,她将现实主义和先锋绘画合并,创造出迷人作品,呈现了对精神、巫术和意识更高境界的追求。在1958年的作品《鸟的创世》(Creation of the Birds)中,她画了猫头鹰一般的生物,以及音乐、星光和飞鸟。在1958年的《天体奶粉》(Celestial Pablum)中,一位女性坐在星空磨坊里,将被研磨成粉末的星星喂食给笼中的新月。
正如福特所说,“在所有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中,超现实主义者最大程度解放了女性,鼓励她们成为自己,更独立地追随自己的脚步。”
画笔下的悲欢离合
同她们的男性同行一样,这些女性艺术家是偶然地发现超现实主义的。她们用智性的自由和自我发现来抵抗资本主义文化。这种自我解放常常寄寓于受梦境启发的作品,但也同样包括更为微妙的一些感受。
西班牙出生的艺术家雷米迪斯·瓦罗,先是流亡到巴黎,在纳粹占领期间又流亡到墨西哥。她的《女人离开心理分析师办公室》(Woman Departing from the Psychoanalyst’s Office,1960)中,一位身着绿衣的女子在离开无窗的大房子时摘下了她的面具——一张老人的面具——用两只手指夹着,颠倒过来,置于一口井之上。面具苍白如鬼魅,无力阻止它的主人。“这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绘画,父亲角色可以像溜溜球一样甩来甩去,或者干脆扔掉,”福特说,“非常有趣。”
来自芝加哥的格鲁特·阿贝可罗比(Gertrude Abercrombie)1949年创作的作品展示了更单纯的机智:一位身着粉红色礼服的女子,高举双手,仿佛受到了抢劫,她面前是一个蒙面男子,右手比成手枪的形状。这件作品的标题是《求爱》(Courtship)。“她看待生活的方式颇具幽默感。”福特说,她指出了其中的超现实主义元素,一个猫头鹰,一柱灯塔和一只海螺——福特认为那代表着性。
“很多女性一生经历坎坷,她们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审美方式,作为和内在问题、过去与未来对抗的方式,试图以此治愈心灵,创造出新的身份。”福特说。
本次展出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抽象的较少而具象作品居多。肖像、家庭生活、超现实主义游戏等主题逐一登场,最后,则与19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挂上了钩。随着女性主义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超现实主义女性画家最终也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中产阶级的陈规戒律。
展览的庞大规模为弗里达·卡洛,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提供了绝好的艺术归属。她的7幅作品中,有一幅描绘了纽约社交名媛多萝西·海尔(Dorothy Hale)从摩天楼纵身跃下。
和那么多超现实主义女性画家结伴,弗里达终于可以摆脱世人对她奇异身世的追索,将人们的关注引向作品本身。
- 推荐关键字:展览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手艺农村项目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大展(图)
- 2012-02-06
- ·洛杉矶正成为艺术市场的新大陆
- 2012-02-06
- ·排队6小时只为敲章 世博会纪念展方呼吁更关注展览内容
- 2012-02-06
- ·女性策展人叱咤国际艺坛
- 2012-02-06
- ·钟长生诗书画在河北全面亮相
- 2012-02-06
- ·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兽首玛瑙杯"身世成谜(图)
- 2012-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