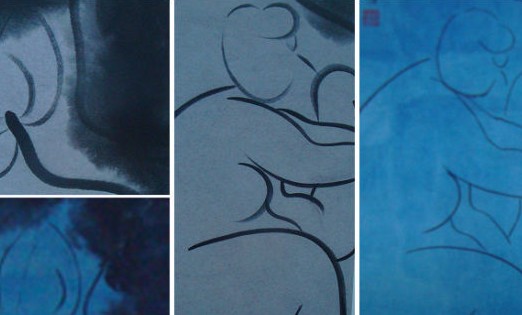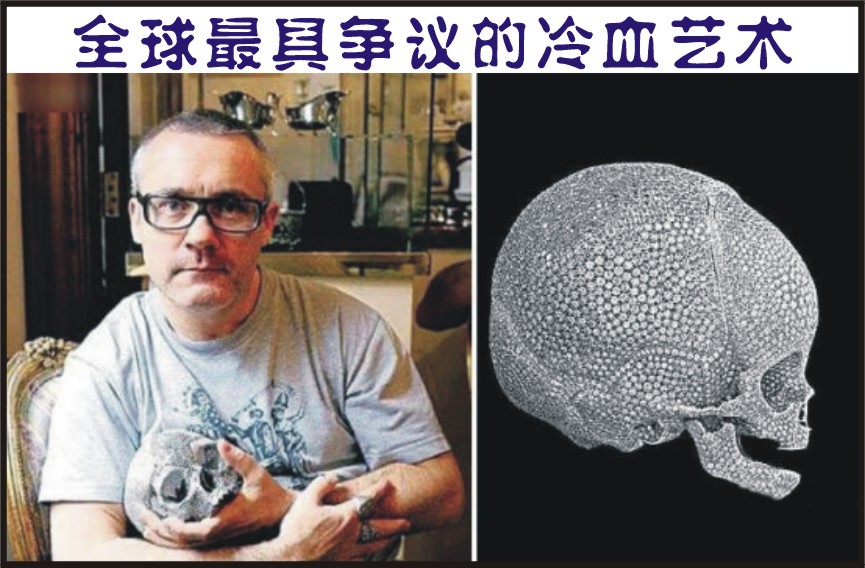玛索琳娜说:“我们不受江青的喜欢。”伊文思夫妇曾在新疆住了很长时间拍片子,玛索琳娜上街拍照,一直有人跟踪,她怀疑是江青派来的,就把跟踪的人也一并拍下。“我觉得我们当时都被当作间谍了,我不是在控诉江青,只是当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被卷入其中。”陆颂和解释,这只是玛索琳娜的怀疑,当时跟着她的是保卫,也没有人把他们夫妇当作间谍。
1975年,《愚公移山》拍好了一部分,伊文思夫妇想放映这些段落,以便知道中国观众的意见,但被阻止了。文化组要审查《愚公移山》,提了61条修改意见。例如伊文思在大渔岛跟船下海,问船长:“你对‘文化大革命’理解吗?”船长说不理解。审片组的意见是:“不可能有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已经拍好的部分几乎全部被批评了,但是伊文思夫妇拒绝任何修改意见。
安东尼奥尼《中国》的盛名,和这部影片曾在中国受到大规模的批判有关,伊文思夫妇也牵扯其中。江青组织不同单位和学校去看《中国》,看完了要批评,并要求伊文思也加入,让他们写文章反对安东尼奥尼。伊文思给出的回答是:“批评别人不是我们的习惯,我们拒绝写批评文章。”玛索琳娜回忆时解释:“都是电影人,我们不能批判我们的伙伴。我们是自由的人,别人跟我们一样自由。”伊文思夫妇在中国的拍摄经常涉及到政治,玛索琳娜说:“历史要比我们讲述的更复杂。”
被指“撒谎”的伊文思
《愚公移山》1976年在法国公映,起初很引起轰动,西方人终于看到隔着铁幕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电影在巴黎放映了六个月,场场满座,收到来自各国的购买要求,电视台也准备播放。当时的评论说:“伊文思把我们带到中国,让我们和中国人生活了一段时间。”
上世纪70年代拍摄纪录片期间,伊文思虽然生活在中国,对政治新闻反而没有国外知道得多。陆颂和回忆,林彪坠机的事情,当时他们对伊文思是保密的:“我们有外事纪律,不能讲就是不能讲,他一点也不知道。”1976年西方开始猜测中国政治变局,伊文思在电视台发表演讲,称“以伊文思的声誉保证,中国政府是稳定的,党是稳定的,不会有变化”。不久后,“四人帮”倒台被捕。
伊文思在西方的形象忽然变成了“撒谎者”、“宣传家”,西方人指责他给中国涂脂抹粉,怀疑纪录片的真实性,《愚公移山》也随之名誉扫地。 伊文思夫妇在随后的十年里都没有工作,生活贫困。1989年,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即便是今天的中国人,看到《愚公移山》,都会觉得有些地方很意外。《球的故事》中,北京一所学校规定上课铃响之后不能再踢球,一个学生还是踢了一脚球险些伤了老师。老师没收了所有学生的球,学生不服。另一位老师因此组织了一场班会讨论这件事。最后双方都反思了自己的不当之处。其中冷静、平等的氛围让人难以置信这是“文革”时的中学。《上海第三药店》中,顾客和村民都派代表到药店开会,给药店的经营提意见,药店则虚心接受。药店的女工收入稳定、生活小康,在家扭开音乐坐下休息,丈夫端着搓衣板出去洗衣服。
玛索琳娜一再强调自己当时对“文革”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们的行动自由是相对的,当1967年有斗争的时候,中国的大门还没有向我们夫妇敞开。有那些斗争的时候我们不在中国,我们只能拍摄能看到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看到《愚公移山》的全部,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也拍到了当时中国贫穷的一面。但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看到全部影片。”
《愚公移山》的名字来自于毛泽东1945年的讲话《愚公移山》,全长12个小时,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大庆油田》、《上海第三药店》、《上海汽轮机厂》、《一个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一座军营》、《对一座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剧团排练》、《北京杂技团的训练》、《手工艺艺人》。拍摄足迹则遍及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受访者有当时的工人、农民、渔民、教授、学生、解放军战士、售货员、演员、手工艺艺人。70年代中国社会的风貌,在其中体现得很多。但是市场上至今找不到这部纪录片的全部,有人怀疑伊文思夫妇不愿意公布。
玛索琳娜说,他们从来都希望大家能看到完整的《愚公移山》:“影视界不要认为我们自己不想出版这些影片。我们希望这些电影能被大家看到,现在只是资金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大家认为,别人说我们是错的,我们就把错误隐藏起来不给大家看。当资金有条件的时候,我会出一个全集。”
伊文思相信“文革”
时代周报:我看到有报道说,伊文思一直相信毛主席语录?
玛索琳娜:伊文思相信的不是毛主席语录,但他相信“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根据官方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民主和给人民更好的生活。当时中国在反苏批修,伊文思相信修正主义确实存在,中国是通过“文革”寻找出路,给人民更多民主。现在中国有很多学者投诉我们,认为伊文思的想法不正确。我们希望大家看问题能公正些。首先是公正,其次是自由,然后要更多的民主。我们到中国是带着这种想法来的。
时代周报:你们曾受到很多攻击,说伊文思是在撒谎,在十年里都没有工作,但你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玛索琳娜:信念。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要这样去做。我15岁的时候就被关在集中营,我家里有45个人都在集中营里被杀害。为什么我还活着呢?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那活着干什么呢?我和伊文思在一起,有很多哲学上的思考。我们不断拷问自己,在思想上往前走,可能一个人走得快一些,另一个人就会很快跟上;一个人有了灵感,另一个人就会有新的想法。
- 推荐关键字:文革 纪录片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电影海报的收藏魅力
- 2006-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