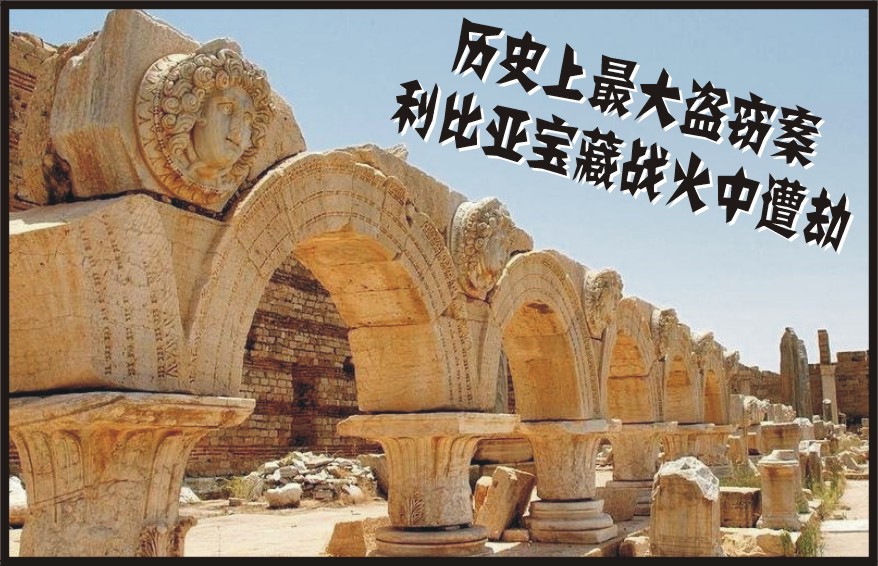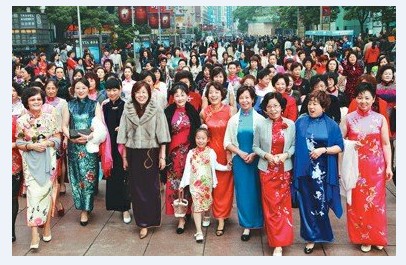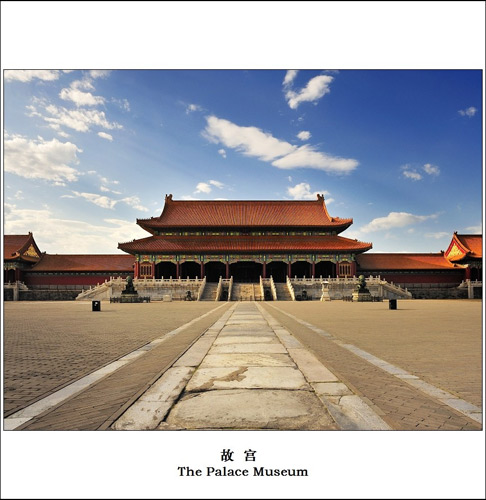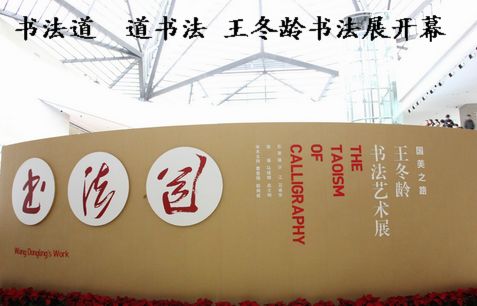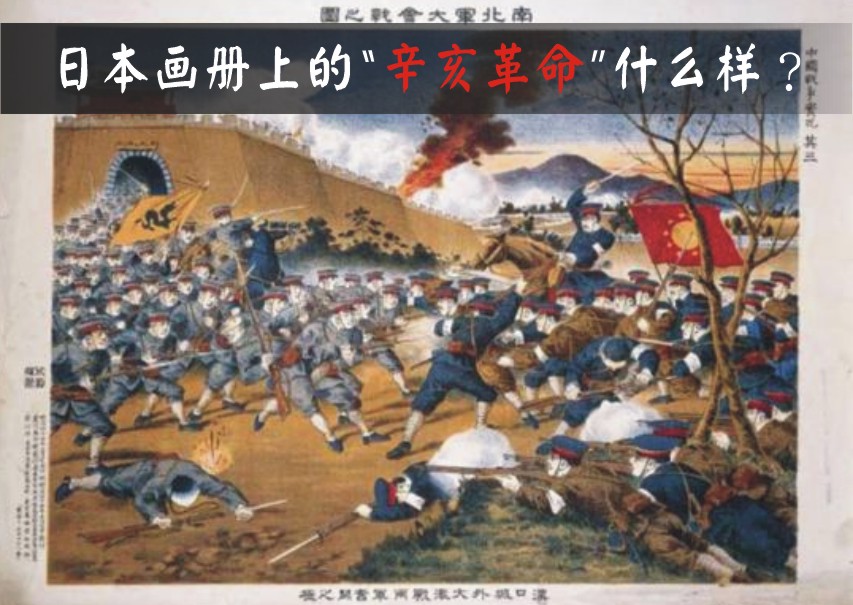《张爱玲》
微薄中的田禾,是一个有着人文关怀和正义感的艺术家;现实中的田禾,是一个脸上洋溢着真诚又温情的女性。她个人的雕塑展览《相》,近日在北京三里屯的以太空间画廊展出,让大家看到作为雕塑家的田禾。
田禾的父亲田世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近年旅居海南潜心创作,田禾也有机会到海南,因此笔者有幸见识田禾颇具家学渊源的创作。或许田禾也有机会到海南是源于家庭氛围的熏陶;或许是遗传自基因;又或许是天赋的创造能力,还有对形体造型的敏感,雕塑于年少的田禾,是一项可以糅合童真乐趣和审美意识的玩意儿,在当中,她得到认何、奖励和鼓舞。田禾读小学二、三年级时,其作品就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无论国内外,女性从事雕塑艺术工作不在多数,因为雕塑相比于其他的造型艺术来说,真是个沉重的体力活。另一方面,雕塑属于三维空间的艺术,有人说,女性对平面的组织能力要比三维强。对此言论,并未得到科学的证实,则无从考究,但相较于其他造型艺术而言,从事雕塑创作的女性确实是少数。田禾便是这少数中的年轻的一员,她生于1978年,在大学期间主修油画,可是从小到大她更爱雕塑。
田禾的雕塑作品给人一种温情和关怀,它们不造作、不矫情、不夸张,每件作品都有着不同的材质和独立的表现方式,田禾总是尝试着各种的可能性;而每件作品也都有着属于田禾的个人视野的解读。叙述者田禾用真诚和热情去体会着世界的万千,当她受到触动的时候,心底便有了翻江倒海的情愫和倾诉的欲望,她要告诉我们她的收获和感动,用她的雕塑来向我们演绎她所遇到的这些人和事。
跟田禾聊天,她的关键词离不开“真诚”和“真实”。在她的眼里张爱玲、南丁格尔、昂山素季等女性都是真诚的,她们对自己的热爱和信仰的坚持皆源于忠实于自我的勇敢,从而形成一种以柔制刚的穿石之力,这样的力量感动着田禾。她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了真实就不再有感动;没有了真诚就不再有美,人与人之间温暖的关系都来源于此。因此,田禾的雕塑虽有着女性特有的细腻,在细节中所流露出的情感却不全是温情脉脉,它们带有思想和批判,也有某种温顺之下的反叛。
《相》是一个由田禾内心而来的百态,它集中体现了田禾成长路途里的思考和变化。在她学院派扎实的写实风格中,并存着她的坚韧、乐观和温情,形成禾田式的风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与人之间,哪怕隔越了时空都会寻找到可参照的镜子,如果内心没有了被感动的触觉,也就不具备这些从心而来的《相》。
田禾的《吹泡泡》系列和《美少年》都是她近年的作品,它们应用了许多非传统的材质,包括玻璃、树脂、不锈钢、琉璃……让雕塑具有透明的感觉。这种由材料而来的尝试并不新奇,却强烈地作用在观众的思维上,它们诠释了田禾的另一个关键词:“易碎”。《吹泡泡》描画出一种单纯的美,它占用了展厅的一半场地,不同的“泡泡”在画廊的场地中树立成高高低低的圆圈,充满着孩童的趣味。田禾觉得生命、感情都是易碎的,它们不能永恒地存在,但其精神可以被转化和延续。她说,我们不能因为泡泡会破碎或幻灭而放弃,即使这是阿Q精神也是值得的。
拿《吹泡泡》和《十九岁》相比,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十九岁》是田禾在她十九岁时的一个老作品,当中那个昂着头的少年一副无畏无惧、坦荡荡的样子,造型朴质而手法老到。我们会惊讶于一个少年能如此把握人物的神髓,哪怕现在看来,它仍然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品。而《吹泡泡》却收敛了《十九岁》的张扬,只显露出天真和稚气,这种稚气有如返璞归真的一个顽皮的回转。将《十九岁》的单纯变作《吹泡泡》的简单;将《十九岁》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变作《吹泡泡》的美好、欢愉和坚定。相隔十年的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颠倒?或许是田禾经历了许多之后,由心而来的转变,她不再是十九岁的少女,但她更懂得生活的要义。《十九岁》的勇气带着涉世不深的无知,而《吹泡泡》的勇气则是对生活的坚持。显然地,个性上的成熟使田禾更懂得对生活的进取和乐观,这样的品格在田禾的身上是显而易见。
我总相信古人言:“相由心生”,每个人的“相”都深刻地刻上人所经历的一切。作为雕塑家,尤其是肖像雕塑家,他们在千千万万的人群中寻找由“相”而来的动人故事,它们首先感动着雕塑家自己。尔后,雕塑家又去刻画和描绘这些“相”,并参合着他自己内心的“相”,也就是艺术家本人的情怀和对美丑的评判,最终,雕塑家成了一个综合“我相”与“他相”的演绎者。田禾就是这样一路寻来,纪录着,感怀着……
- 推荐关键字:雕塑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中国美术“国家形象”全面呈现 千余作品展国博
- 2011-11-01
- ·疯狂红色弧线塔在英国亮相(图)
- 2011-11-01
- ·中国国家画院建院30周年青年美术作品展在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图)
- 2011-11-01
- ·中国国家画院建院三十周年庆典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图)
- 2011-11-01
- ·东方既白——中国国家画院建院30周年美术作展亮相国博(图)
- 2011-11-01
- ·79件顶级艺术品下月亮相深圳(图)
- 2011-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