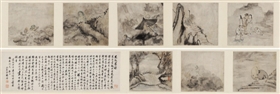
《鬼趣图》手卷,罗聘作
在清代的绘画史上,有八位著名的画家——汪士慎(巢林)、黄慎(瘿瓢)、金农(冬心)、高翔(西堂)、李鱓(复堂)、郑燮(板桥)、李方膺(晴江)和罗聘(两峰)。八人当中,除了高翔祖籍扬州,李鱓、郑燮为扬州兴化人外,其他都是陆续寄居在扬州的。他们大都出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三十四年(1695)之间,长期活动于扬州一带,意气相投,关系密切。艺术上相互切磋影响,诗、书、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貌和情趣,成为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人们习称为“扬州八怪”。

《林下清风图》,金农作

《双松兰竹图》,郑燮作

《八仙图》,黄慎作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扬州由于盐业和其他商业的发达,成为东南地区数一数二的大都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纷纷涌向扬州谋生,一时呈现出艺苑争雄、各斗新奇的局面。然而,在当时歌舞升平的背后,却是官场的污浊黑暗、盐商的骄奢淫逸和农民的饥寒交迫。“扬州八怪”中的大多数人出身贫寒,后来又一直当“布衣”,虽然都是享有盛名的大艺术家,有时也要挨饿,以致有人写诗怀念罗聘说:“画笔压当世,寒饿犹难免。”这可以看作是对“扬州八怪”的真实写照。李鱓、郑燮、李方膺三人虽然当过七品芝麻官,但都想切实做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因此得罪了上司,丢了官。他们看到社会上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心中甚为不满,但与此同时,对平民百姓又寄予了同情。在这点上,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相传郑燮初到范县上任,笫一件事就是吩咐把衙门中四周的墙壁都打上孔洞,一共打了百把个洞,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外边的街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打洞,他回答说:“放出些前任官的恶习俗气罢了!”乾隆元年(1736),金农刚满五十岁,有人荐举他去应博学鸿儒科的考试,这是非常“体面”的事,考上了,马上可以当上翰林官。金农力辞不就,却又骑了匹蹇驴上京去,别人问他既然不去应试,干么又上京去?金农说:“我要去看看那些应考的究竟是些什么人!”这种言论行动,在当时是有点离经叛道的,自然要被认为“怪”了。
“扬州八怪”之“怪”,不仅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主要还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作为诗人,他们注意反映民间的疾苦,抒发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内容。黄慎在一首短诗中写道:“黄犊恃力,无以为粮;黑鼠何功,安享太仓!”把贫苦农民比做黄犊,把官僚比做黑鼠,爱憎何等分明。郑燮一生写了许多诗文,他说过“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话,写过“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之类的诗,确实都是“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感人之作。但是,作为书画家,他们的创新精神就更突出,影响也更为深远。
清初,画坛上崇尚的是以王时敏为首的“四王”的画风,以临摹为高,讲究笔笔要有来历;书法界则奉董其昌为宗师,欣赏的是那种姿媚靡弱的笔致。等到“扬州八怪”兴起,努力标新立异,对当时的画风书风提出挑战,继承了徐渭、朱耷、石涛等人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主张师造化,法自然,要从生活中获得真实感受,寻找创作题材。这种创作方法也被认为是“怪”的。
金农拜竹为师。春天来了,他到处去求竹种。听说龙井山僧的竹是一种稀有的品种,就长途赶去购置。人家要价昂贵,每一竿要卖青蚨(细钱)三千,他倾其所有,买来竹种,栽在书堂前空地上。从此,他每日白天徜徉竹林中,细心看竹,夜晚坐看窗上竹影婆娑,睡在床上还倾听着风吹竹动的声音。病了,不愿迁入内室,说:“我不可一日不听风声竹声。”“扬州八怪”都注意认真观察事物,表现在画面上,尽管是一枝片叶,也都带着感情,做到“物我交融”,在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中寓有丰富的主观意趣。
“扬州八怪”中除了黄慎、罗聘兼擅人物、山水、花果外,其余的多喜作“四君子”(梅、兰、竹、菊)。笔墨淋漓、奔放奇崛,这是他们共同的画风。但也要看到同中有异,各具面貌。比如画梅,汪士慎喜画繁枝,千花百蕊;高翔多作疏枝,抹红一点;金农常画野梅,瘦枝繁花,李方膺则喜作丈许大幅,蟠塞夭矫。李鱓与郑燮交好,李工画兰竹,他看到郑燮所作的兰竹,跟自己的面目完全不同,另具一种风致,就高兴地说:“这是能够自立门户的!”这里,可以看到,“扬州八怪”是多么重视作画的个性特点啊!
罗聘是金农的学生,他爱画鬼。他的《鬼趣图》非常有名,那是因为他借鬼喻世,别寓深意的缘故。如他画一个鬼,鲜花插头;一个鬼,赤体戴帽相随;题曰:“主人衣服丽且都,其仆乃至寒无襦。”他又说,鬼如碰到“富贵者”,就靠着墙壁蛇行而过,如遇着“贫贱者”,那就动手动脚,百般捉弄。这哪里是在画鬼,分明是借助于鬼的形象来描写人间,抨击社会!
“扬州八怪”在书法上的创新也很突出。金农古拙厚重的“漆书”,被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誉为“逸品”。郑燮的字,篆、隶、楷相参,布局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自称是“六分半”书;黄慎喜学怀素狂草,他的画幅上常作草书长题,显得映衬有致,受到鉴赏家的重视。
“文人相轻”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的一大通病。但是,郑燮却另当别论。他非但与扬州画派诸家十分友善,而且与社会上其他品才兼优的文人均很要好。平时常“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墨林今话》),即便是当县令时,“公余辄与文士觞咏”(《兴化县志》)。可谓是“文人相亲”矣!诗人马日琯就是在庙中与他对诗结为挚友的。他与西江程羽宸也有知遇之恩。在他落魄之际曾得程千金相助,“扫开寒雾”“一洗穷愁”,甚至睡觉亦“屡梦公”。而他对有才华的晚生也是十分器重。有秀才要进京时,他则亲自烹鱼煮酒相送,并介绍到京后的安身和学习的地方。他与“扬州八怪”中的书画家、鉴赏、篆刻家金农感情更深。两人在扬州时可以说无话不谈,形影不离。郑燮到潍县后,误听金农死了,立即披麻设祭,哭得死去活来,后得确信是虽病未死,遂转悲为喜,寄书问候。金农也十分感动,立即挥书致谢,并将自画像寄给他留念。“扬州八怪”中的另一位书画家兼诗人李鱓,与郑燮命运几乎相同。他也当过县官,也因触大吏而罢归。两人常一起作画论艺,互相切磋启迪。当郑燮晚年生活无着时,便住在李鱓家。他们情同手足的事迹,被艺林传为美谈。
“怪”应该理解为“新”。发扬了艺术的优秀传统,敢于创新,这是大好事,何“怪”之有!事实正是这样,“扬州八怪”对近代花鸟画的影响非常深刻。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都从他们身上吸取过养料。近代南方绘画之能摆脱正统画风的束缚,独树一帜,“扬州八怪”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 推荐关键字:笔墨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