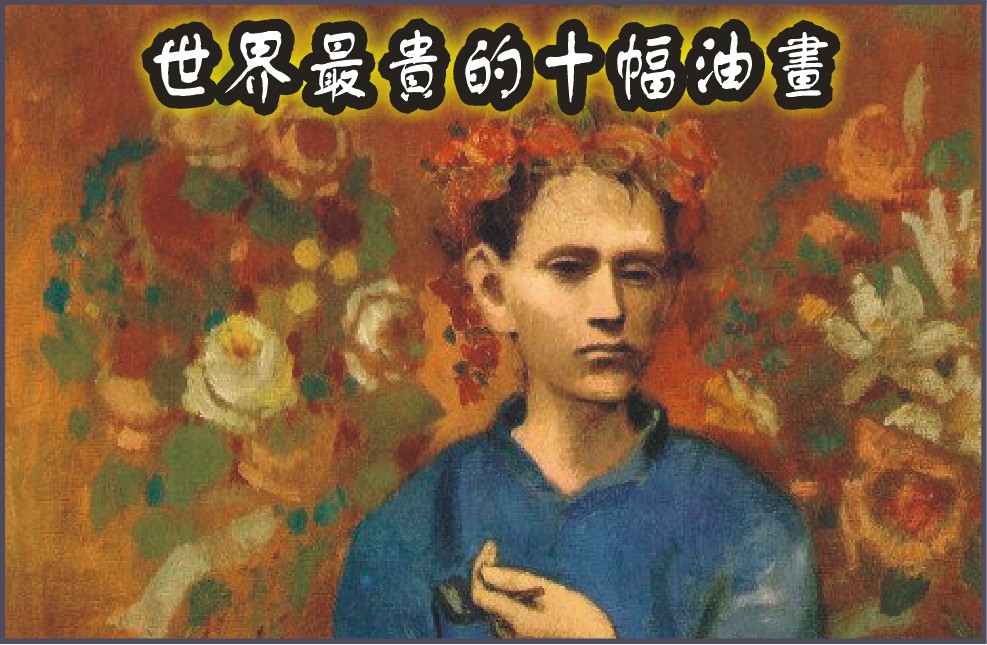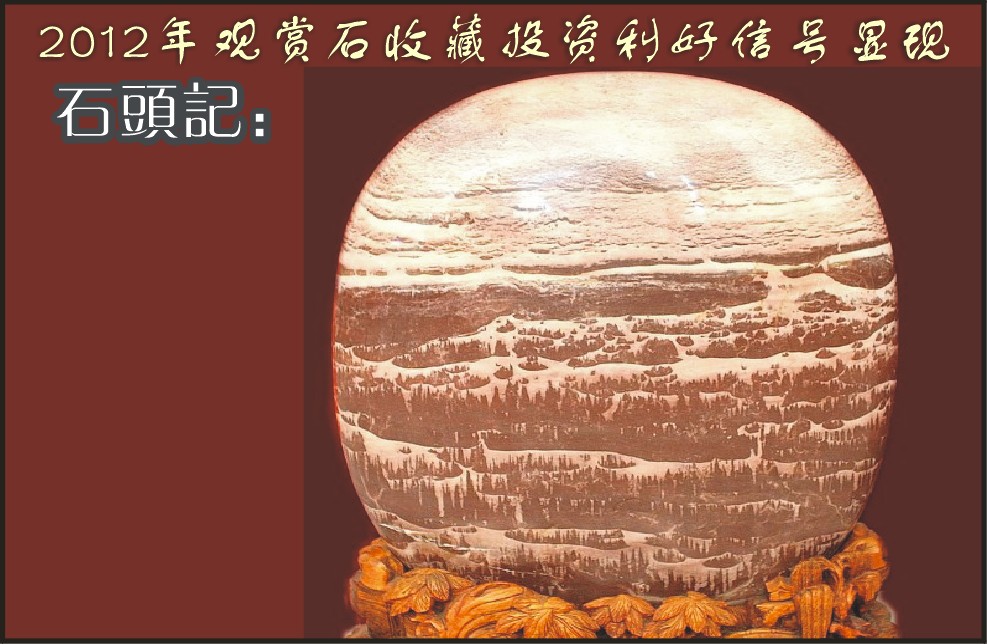当我5年前在搬到这附近时,这里全是电器用品店、被遗弃的房间以及抽烟的人。我的房间里没有暖气;朋友们从来不会晚上来看我;我的一个邻居曾用一把小刀袭击了另一个邻居。而现在,我再也没在伊斯坦布尔看到任何刀剑等武器了——我倒是看到了更多的艺术。
11月的一个晚上,当地的土耳其人以及慕名而来的国外游客纷纷来到SALT巨大、厚重的大门前,准备参加它的开幕派对。其中一场开幕展展出了数千张黑白摄影作品,它们都是由一位已经去世了的美国影棚摄影师拍摄的,再由年轻艺术家Tayfun Serttas收集整理到一起。另一场开幕展则展出了土耳其当代艺术的老前辈——艺术家Gulsun Karamustafa的装置作品。还有一场开幕展则是关于古文化以及欧洲人打劫奥斯曼帝国的。
不过,整个空间的气势完全压倒了艺术——它太过壮丽庄严了。伊斯坦布尔以前根本没有像SALT这样的事物出现过。建筑内部一共有5层,还有10万平方英尺的地方布满了白色大理石雕刻。当策展人、银行家、室内设计师、作家、音乐家、学者、艺术家以及富有的妻子们走上华丽的楼梯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脖子去看高高的天花板。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风格独特的图书馆和豪华的影剧院,吸烟平台同时被用作了餐厅。
大批国外游客在获得了许可之后也进入到了建筑内部。即使是相信宿命论的土耳其人——他们对西方人的热情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承认这座奇特的艺术机构简直棒极了。从19世纪的世界性仙境发展到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用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家Orhan Pamuk的话来说——一座“苍白、贫穷、劣质地模仿了西方国家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似乎来到了它的重生时刻。这些东方新兴的富有的角落似乎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然而土耳其人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文化呢?在我出来的路上,我碰到了纽约303画廊的资深总监Mari Spirito。她不久前才到土耳其创立了一间名为“Protocinema”的非营利艺术空间。在我们的头顶上,阿拉伯字母被深深地蚀刻到了大理石之中:“赚钱的人都是上帝心爱的仆人。”“纽约最好的年代似乎已经离我们而去了,”Mari Spirito说。“而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年代还没有到来。”许多土耳其人会开玩笑地说那些最好的年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这的确是一个伊斯坦布尔的年轻、有天赋的艺术家应该感到兴奋的时期。
在去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期间——现在它已然发展成了一场著名的国际性盛会——土耳其总理夫人Emine Erdogan裹着头巾在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这是伊斯坦布尔主要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了一次演讲。言论自由对于政治来说也许是件坏事,但当代艺术对于商业来说却是大有裨益的。不过,伊斯坦布尔政府与艺术界里企业赞助人复杂的关系会给艺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另一回事了。
伊斯坦布尔的艺术分布状况
有一部分近期已经缓缓进入了某些年轻艺术家的生活中了。几个月前,我曾在artSumer画廊见到了艺术家Gozde Ilkin的作品。她为展览取名为“避难所:来自内里齐声合唱(Refuge: Chorus of Voices From Inside)”。在这场展览中,Ilkin将一对新郎和新娘、土耳其男人跳舞的轮廓缝制到了带有过时图案的床单和窗帘上,这些床单都是在她家中的衣橱里找到的。而这些轮廓则来自她在照片里见到的真实场景。在另一件作品中,她又将微型坦克、直升飞机以及士兵的样子缝制到了一块窗帘橘色和棕色的花纹中。这一系列名为“窗帘:它们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Curtain:They Were Sleeping Somewhere Inside of Us)”的作品似乎很受观众欢迎。“所有的作品在展览开幕之前都卖光了,”该画廊的画廊主Asli Sumer说。
“看到了吗?这就是疯狂的伊斯坦布尔。”国际艺术顾问Patrick Legant对我说到,他在苏富比(微博)伦敦工作了10年的时间,几个月前搬到了土耳其。
目前,像Gozde Ilkin这样的艺术家(Ilkin今年31岁)面对的机遇和诱惑是其它时代的艺术家从未体验过的:非营利的艺术空间,媒体关注,各种聚会、演讲、拍卖会;总是有能够阅读的新的书籍,能够彻底查看的档案资料,前辈艺术家的作品总览等等。此外,某些艺术家还获得了经济上的奖赏:在Ilkin的展览开幕数周后,她的一件作品在伦敦苏富比以1.2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这样,Ilkin——她同时还是艺术组合AtilKunst的成员之一,该组合通常会花时间来制作政治张贴物或是推出免费观看的行为表演——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以艺术家的身份谋生。“当我卖出我的第一件作品时,我竟然觉得很悲伤,”Ilkin说。“我着迷于我所做的事,要为作品定价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她没有将所有的作品都用于出售:“保留自己的一部分作品对我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些艺术家对这个曾经被世界遗忘过的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了解。“情况完全不同了,它现在已然成为了一个市场,”Yasemin Nur说。“这与上一次经济危机联系到了一起,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已经成为了一个时尚的城市,这似乎是它命中注定的。整个体系需要这个时尚的城市,下一个也许就是贝鲁特,或是其它的什么地方。现在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愁思终将被风带走。”
伊斯坦布尔艺术圈的核心在上世纪80及90年代时通过某些重要人物的努力被结合到了一起,这其中包括策展人Ali Akay与Beral Madra,艺术家Halil Altindere,SALT总监Vasif Kortun等等。大多数艺术家都会告诉你今年53岁的Vasif Kortun是伊斯坦布尔的艺术界之父。“我们可以这样告诉你,Vasif贯穿在了整个过程中,”其中一位艺术家对我说。另一位艺术家则表示:“在以前,如果你想在国内或国外举办展览,你都需要Vasif的帮忙。”Vasif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他似乎能够预测出艺术体系的发展方向,”以贝鲁特为基地的评论员Kaelen Wilson-Goldie说。
1998年,Vasif辞去了他在纽约巴德学院策展研究中心博物馆的工作,回到贝约格鲁创办了一间小型的工作室。他为其命名为“伊斯坦布尔当代艺术项目(Istanbul Contemporary Art Project)”,后来这里成为了伊斯坦布尔最早的艺术中心。随后在土耳其担保银行的支持下,Vasif创立了Platform Garanti,这是一个同时还能存档书籍、评论以及艺术家创作材料的展览空间。Platform Garanti在2007年时关闭了,2011年,Vasif又和银行方面合作创立了SALT Beyoglu以及SALT Galata。它们被打造成了“用于研究和进行实验性思考”的地方,花费了大约3000万美元建成。
如果档案馆与图书馆是一种焦点的话,那是因为很少有机构注意到土耳其的历史。“我们总是希望能在伊斯坦布尔创造这样一个地方——它拥有各种各样的材料供人们进行研究,”Vasif说。“80年代那一批概念化的艺术家没有被评估过,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市场性的艺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一段困难的时期,当时的人们对他们的作品也很冷漠。因此我们需要数字化整个档案。”这样的忽视远远超出了80年代的范围。“如果你将奥斯曼帝国看作是一幅地图的话,我想其中最不显眼的地方便是伊斯坦布尔以及那些来自土耳其的艺术家。”
土耳其的知识分子们将伊斯坦布尔缺乏真正的现代与当代文化归因于它残缺的历史。即使是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土耳其人依然承受了许多更加暴力的干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亚美尼亚人与希腊人的大屠杀、与库尔德人的内战、三次军事政变等等。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造成了连贯的土耳其文化的缺失。
“伊斯坦布尔太过肤浅了,”Vasif说。“它不是一个依靠智力取胜的地方。它是一座同时带有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犹太人的老城。亚美尼亚人是这座城市的‘知识骨干’,这里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就失去了它赖以呼吸的东西。也许还不止如此。它从一开始就是残缺不全的,20世纪是这座城市的失落世纪。”
在压抑的土耳其政府出现之前,“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这一老套的言论就理想化了君士坦丁堡不真实的过去。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使伊斯坦布尔的艺术家融入到了国际社会中,他们也会回归到去重新发现自己。“这不是一场革命,”Vasif在谈到伊斯坦布尔现阶段的文化生产时说。“这实际上是一种修正。”
- 推荐关键字:当代艺术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赫尔辛基摄影双年展开幕 展当代艺术作品(图)
- 2012-03-09
- ·艺术酒店正变身为可居住的美术馆
- 2012-03-09
- ·"2012年草场地摄影季·阿尔勒在北京"四月开幕
- 2012-03-08
- ·绘画与摄影的124年纠结——谁比谁更艺术(图)
- 2012-03-08
- ·财富新贵变身超级藏家 "鱼和水"的动力与影响(图)
- 2012-03-08
- ·一间画廊的关闭如何影响艺术市场的食物链(图)
- 2012-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