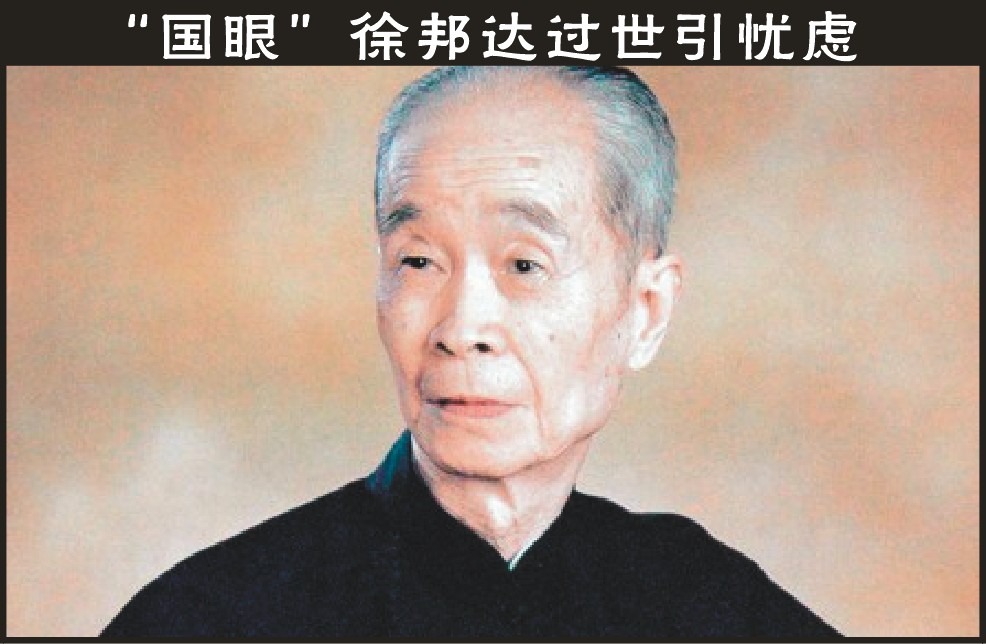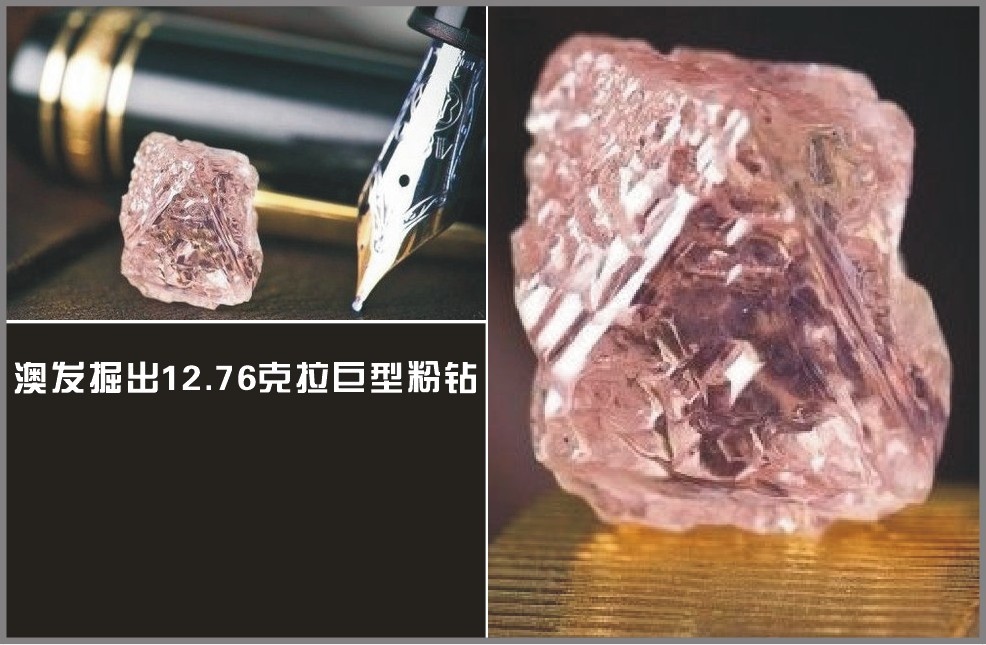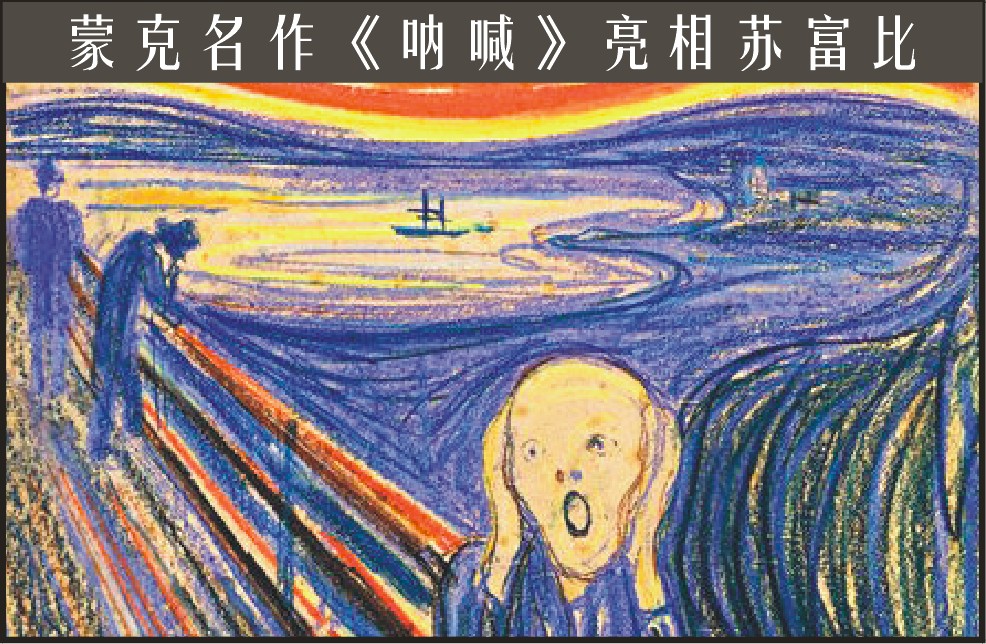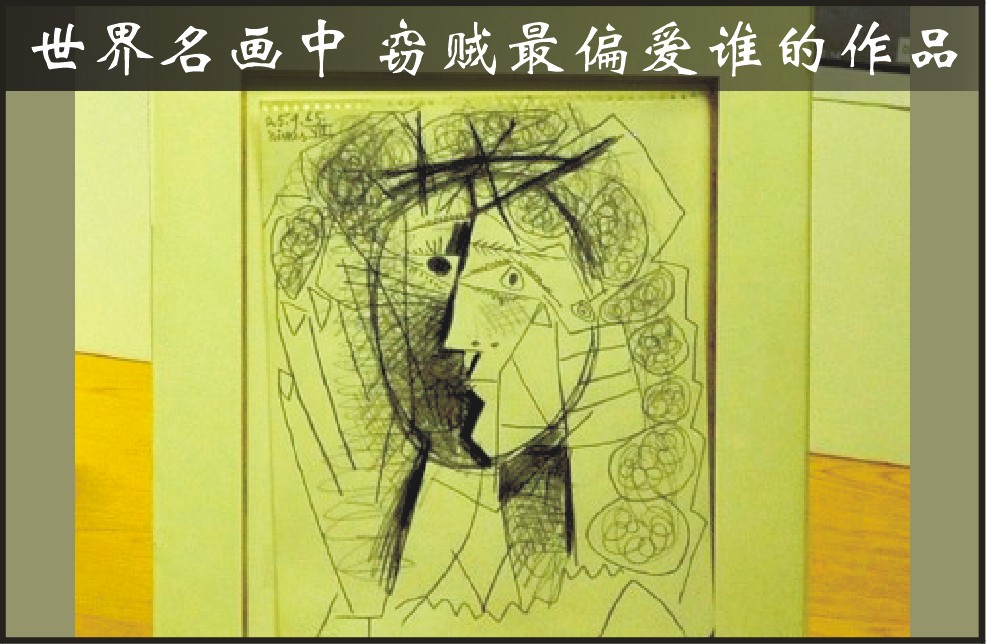古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去世
http://www.socang.com 2012-02-24 13:48 来源:东方早报

徐邦达,中国书画鉴定大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2012年2月23日在北京去世
2月23日上午8时38分,古代书画鉴定大家和知名书画家、百岁高龄的徐邦达先生驾鹤西去,与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魂归一处。至此,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五位“掌眼人”悉数作古。
“从1月19日开始,邦达先生都是住在家里。虽然插着管子不能说话,但思维很清醒。每天睡觉前,我都会去跟他告别,会轻轻地亲吻他一下。”徐邦达妻子滕芳女士昨天说,“(23日)早上8点38分,徐先生离开得很安静。早上我坐在他床头的时候,他的体温已经很低了。我贴在他耳边和他说,‘一路走好,一定要高兴,一定快乐,一定要找到另一个你喜欢的极乐世界。’这就是我对他最后的祝愿了。他这一辈子很简单,很快乐。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对于他这一生从事的事业,他也是从内心上热爱和高兴。他一生都是为书画这件事,他自己常和我说,这既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梦想。”
书画家、鉴定家劳继雄是谢稚柳的学生,从1983年起跟随谢稚柳、徐邦达、启功等在全国鉴定10余万件书画作品,回忆起徐邦达的点滴,他昨天对早报记者说,“徐先生脾气特别好,从来就没见他发火,他后来与谢老有一些分歧,但主要都是学术鉴定之争,而不存在派别之争,比如,他对我们后一辈就特别关心,他还曾经考过我,在我鉴别无误后,徐邦达说,‘你要不是谢老的学生,我就不考你了。’”
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负责人董国强昨天说,艺术市场上,徐老的鉴定可谓金字招牌,甚至对他鉴定意见的信赖超过很多民国甚至清代鉴定名家。对古书画鉴定而言,随着徐邦达先生的离去,五老尽归道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徐邦达,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号蠖叟,浙江海宁人,1911年7月7日生于上海。其父徐尧臣经营丝绸生意,虽为商贾,却性情儒雅,喜好文墨书画,闲暇时热衷于收藏,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便会不惜重金购进收藏。自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徐邦达耳濡目染便也喜欢上了字画。据徐邦达生前自述:“父亲看我喜欢,就在我14岁的时候为我请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李醉石(李涛)、赵叔孺(赵时棢)等先生,教我诗词歌赋及绘画。又入上海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学习书画鉴赏。后来慢慢地对书画鉴赏就有了一些认识,自己也开始买书画,及给别人鉴定字画。”
苏州画家李涛为“娄东派”后劲,他授徐邦达作山水画,让其系统地临摹了历代山水圣手名作。而赵时棢则长于古书画鉴别,指导徐邦达对各家运笔技法揣摩鉴别,皆有心得。徐邦达入吴湖帆门下之后,跻身为其门下“八大弟子”之一。此外,也曾师从冯超然、陈定山等名家。得名师指点,又博采众长,年轻的徐邦达画名日隆。与他同时期寓居上海的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人,当年时常在一起雅聚,论书品画,探讨切磋。晚年的徐邦达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同住在上海市武康路一所僻静的小楼中,其中有一间北屋布成日本的榻榻米式,方席寻丈,壁饰诸友合作的长幅杂画,不时邀集斯文朋友,对坐其中,吟诗作画,以消长日。那时经常见面的艺术界朋友有杨清馨、郑午昌、张碧寒、王纪干、陈定山……”
中国传统的书画家无不热衷书画鉴定与收藏。徐邦达家境殷实、交友广泛,更因家庭氛围的影响,自然不免由创作而入书画鉴别与收藏之道。尽管弱冠即从李涛、吴湖帆这样书、画、鉴三者皆长的一流收藏家,徐邦达买到的第一张画却是赝品。那时他年方18岁,由于师承“娄东”,因此也偏爱清初“娄东”领袖王原祁的画,于是当他看到一幅王原祁的画作时就不由动了心,经过仔细辨别,认定它是真迹,便以二十两黄金的价格买下了,但是,此画后来经权威专家鉴定为赝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二十两黄金买了个赝品,教训深刻”,至晚年也常常提起这件事以为笑谈。
事实上,从18岁买下第一张画始,徐邦达在此后的80余年里,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接近4万件。起步时的一次走眼,并没有影响他终成一言九鼎的国家级书画“掌眼人”。而在徐邦达古代书画鉴别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或许当属他识别出真伪《富春山居图》,那距离他买进那件王原祁的伪作才不过5年而已。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当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抓住机会去库房观摩,在那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两幅画上都有乾隆御笔分别题说其真伪。然而,经过徐邦达的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无用师卷》实际却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子明卷》却是假的,这一说法推翻了清朝宫廷的定论,还黄大痴杰作以真面目。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山水合璧”的,即《无用师卷》与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剩山图》旧为吴湖帆所藏,作为吴门爱徒的徐邦达或许曾仔细观摩、体会过图上大痴的笔意。
1937年夏,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之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和陈列工作。这是他正式涉足古代书画鉴别的开端。展览之后,叶恭绰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惜哉,徐邦达的这部处女作成书后即交付叶恭绰,彼时恰逢“八一三”事变,叶恭绰仓皇离沪避难,在途中将书稿佚失了。
至上世纪40年代,徐邦达的画艺已然名噪江南,并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之后,还被聘为上海美术馆筹备处的顾问,并在此期间,于沪上举办了第一场个人画展。
上世纪40年代末,徐邦达从上海市区迁居嘉定县城。在那里,他进行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创作,而其鉴赏水准也随之精进。回忆此间生活,他曾道:“与画友孙祖勃君朝夕过从,讨论艺事,最为欢洽。”与此同时,凝聚徐邦达一生心血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编撰的,而那时的徐邦达并没有想到这部书会延续一生。
1949年,徐邦达和好友张珩(字葱玉)一同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之后,张珩便被调去了北京。张珩与当时的中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熟识,徐邦达与郑振铎的交往也正是始于在张珩上海寓所的一次会面。张珩到了北京之后,更是向郑振铎力荐徐邦达,于是郑振铎就把徐邦达也调去了北京,在中央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主要工作则是收集、鉴定古书画。
据徐邦达生前口述:“我从上海来北京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字画,当时是在文物局工作,在北海的团城。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画都让国民党给带走了,所以我们就要把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字画一点点地收上来。”自那时起,徐邦达的鉴别与收藏行为就与国家力量的支持分不开了。他曾透露过他征集书画的秘诀:“因为解放前我就经常到各收藏家家里去看东西,所以谁家有什么东西心里大概有个数。因此到了1953年的时候,差不多收上来约3700多件东西,这里面有的能捐的我就动员他们捐了,能献的献了,实在不行的就只好买了。”
三年间居然就能征集到3700余件书画,工作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可见一斑,也由此可见徐邦达对此的专注程度。他晚年仍然对在团城倾力工作的那一段日子印象深刻,曾回忆道,曾有一次因为鉴别工作太专心,以至于棉大衣的后背被炉子烧着了他自己居然都没发现。其夫人滕芳也念念难忘有一次,徐邦达感冒发烧,在睡梦中突然大喊“挂,挂”!滕芳问:“挂什么?”他却用手指指墙,闭着眼睛说:“从这边开始挂,唐、宋、元、明、清,依次挂。”
事实上,故宫博物院于1949年之后的所藏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而连做梦都离不开古代书画的徐邦达,在那一时期鉴定并征集到数千件古书画作品。此后这批古代书画都被交拨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并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庋藏中的基本藏品,正是在此基础上,其“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才得以正式成立。
从1983年开始,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开始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鉴定组由7人组成,谢稚柳任组长,组员名单中,徐邦达赫然在列,其他则为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成《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今天,留存在大陆的绝大部分中国古代书画只要一查《目录》就能知晓其传世状况。
徐邦达参与的这一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书画普查,前两次分别在北宋宣和年间和清乾嘉年间,留下了研究传世古代书画必不可缺的参考文献《宣和画谱》与《石渠宝笈》。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也堪与历史上的前两次比肩,成为后人所参考的重要文献,由此可见徐邦达及其同仁谢稚柳等对古代书画鉴别的功力。
在鉴定组中,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五位“掌眼人”各有特点,因此观画的侧重点也不同,如谢稚柳本身即为书画大家,因此侧重画意。而徐邦达师承吴湖帆等“娄东”余脉,为传统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除了对古代文献资料烂熟于心,还独有一双慧眼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有人认为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天赋,可他自己认为“只在用心”。
徐邦达因书画之缘而鉴定,因鉴定而每日里与书画耳鬓厮磨。对于古迹名作,更有摹以乱真的本领。现存加拿大的奚冈《松溪高逸图》摹本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芙蓉鸳鸯图》摹本是他24岁时所临。晚年鉴考之余,重拾画笔,创作山水,笔致秀润,意趣幽深。擅古典诗词。于书画鉴定之外,他更是以著述记录心得,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等著作。
徐邦达曾把古书画的鉴定析为“鉴”与“考”两个概念。“鉴”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进行目力检测,推知真伪。徐邦达的弟子、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曾总结说:“徐先生博闻强识,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其所论所断,使人折服。”
为徐邦达的古代书画鉴别能力所折服的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徐半尺”。据说,这个雅号得名于一次,有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至有“徐半尺”的雅号。而他的弟子说,其实更应称呼他为“徐一寸”,因为书画卷往往展开寸许,徐邦达便已知真伪。
对于谢稚柳与徐邦达鉴定风格的不同,劳继雄认为,谢老是画家的眼光,不轻易否定,而徐老的考据功夫更好一些,两人各有所长,两位老先生当时的争论对大家的启发很大。徐老对代笔问题研究很深,这对中国书画鉴定贡献很大,“他提供了思考的方向,不仅仅是从笔墨技巧看,还要结合历史考据与文献资料。”
对于这几年徐老鉴定的作品存在个别争议的话题,劳继雄昨天认为,鉴定有争论是很正常的,各人的角度不同,各人看的方法也不同,商品社会确实会影响书画鉴定界,但对徐邦达这样的老一辈鉴定家而言,相信他决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把假的说成真的。当然,万一走眼对鉴定家也很正常,徐老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否定自己,因为很多书画通过重新研究,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而书画鉴定是非常个体化的活动,不是标准化产品。
徐邦达90多岁时写了一幅“实事求是”,挂在书房的墙上以自勉,这四个字也是他鉴定原则的写照。
责任编辑:邹萍
- 推荐关键字:徐邦达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中国收藏网的立场,也不代表中国收藏网的价值判断。
相关新闻
- ·古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去世
- 2012-02-24
- ·“半尺大师”徐邦达掩上百岁人生长卷(图)
- 2012-02-24
- ·“国眼”徐邦达过世引忧虑 书画鉴定少壮派何在(图)
- 2012-02-24
- ·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去世 享年101岁(图)
- 2012-02-23
- ·媒体叹艺术圈闹出的桩桩笑话(图)
- 2012-02-10
- ·《雪梅双鹤图》身世离奇:旧纸堆里发现一级文物(图)
- 2012-02-03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