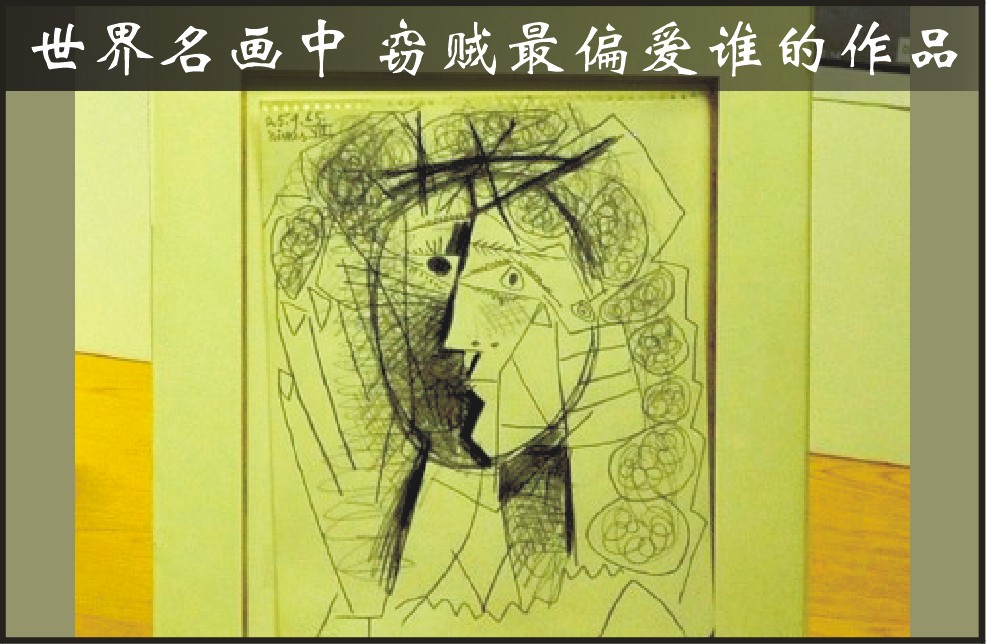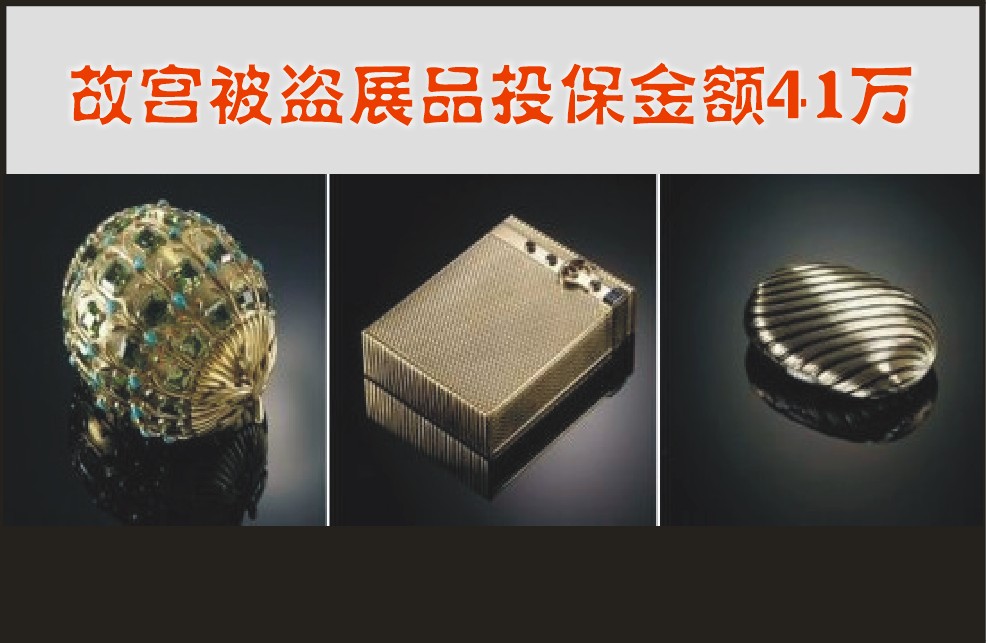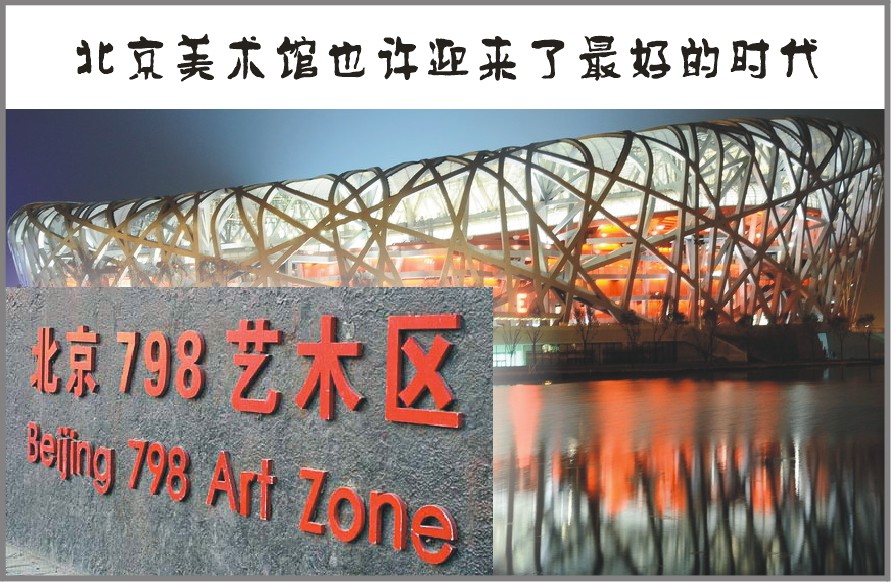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距今五千年或更早,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已经迎来文明的曙光。不过,这两支局限一隅有神权至上特质的文明很快衰落。从公元前2500年前后开始,多种文明因素向中原黄河流汇聚的趋势明显,出现方国林立的初期文明形式。公元前2000年前,随着多元文明因素的汇聚与交融,文明因素的碰撞与整合,中原早期文明的内涵有了质的升华,出现夏文明。夏文明的一个特质,体现在世俗集权形成方面。晋南陶寺和豫西二里头是夏代早晚不同时期的两处代表性遗址,特别是二里头遗址更是研究夏文明起源的典型材料。结合近来新的碳十四系列测年,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可能比过去认识的要晚一二百年。将考古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分析,目前可以说,至少到公元前1800年后,在中原地区,最终出现了夏王君临天下,以国家为标志的成熟文明体。
为什么到了公元前的19世纪,会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统天下,并延续下来的世袭王权,这是新世纪以来,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致力解决的焦点问题。对此,学术界从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区与周边文化区的互动与交融、二里头文化的包容与开放等多角度进行过深入探讨。然而,中原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还有来自遥远的西方华夏文明区域以外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参与和渗透,并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话题,则长时期内被有意无意地回避和忽视。近年来,随着包括新疆在内中亚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随着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外来文化因素的不断输入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起作用和贡献,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而拓宽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首先是史前青铜之路概念的提出和确立。青铜之路讲的史前青铜技术由欧亚西方向东方传播的途径和过程。公元前四、五千年,西亚和欧洲大多数地区的古代居民,开始利用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制造大量青铜器。青铜冶铸技术随着西方人群向东方的迁移,距今4000年以前进入新疆,在东天山地区与东来的彩陶文化碰撞与融合,创新出了具有中国西北原始萨满文化特质的青铜器群。东天山早期青铜器类型繁多,常见的有铜牌饰、管饰、铜铃等生活和宗教饰件,以及以各类铜刀为代表,适应游牧生活的生产工具。重要的发现有东天山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和罗布泊西南发现的著名小河墓地。这两处墓地的最早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出土各种青铜制品数以千计,表现出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水平。新疆东天山地区形成的青铜文化,很快向甘青地区传播,在甘青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学术界早就注意到偏居西北的甘青,史前青铜器群出现年代比中原早,冶铜技术发展到相当高度。针对这一现象,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中国早期青铜技术发展的孤岛,有的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它们的出现与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有关。
甘青与新疆东天山地区的早期青铜器群,无论是铸造技术还是文化风格,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形成了与中原青铜器群相区别的特殊的青铜文化圈,可称为中国西北系青铜器。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的出现,要比中原早期青铜器群的出现早二三百年或更早。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形成后即向北向东传播。北向的一支,主要是沿着黄河,传播到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的其它地区,肇夏商之际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形成之始。东传的一支,很快进入华夏文明延生的核心区晋南和豫西一带。晋南陶寺遗址出土一件齿轮形圆牌饰,是件孤品,由文化风格寻其来源,这件器物更大可能来自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的分布区。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群中有一组特殊器物,包括环首刀、铜凿、长方形镂孔牌饰等,这些铜器在当地没有文化根源,而恰是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的典型器物,其来源也不言自明。二里头青铜群中发现有含砷的青铜器,陶寺那件齿轮形圆牌,也是用砷铜制成。砷青铜技术始源于西方,表现西方青铜技术的特质。新疆和甘青早期青铜器中砷青铜器的发现不断增多,学界普遍认为其与西方青铜技术有内在关系。中原早期砷青铜的发现,可以理解为西方砷青铜技术向东方传播的最外环。早期青铜器问题,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方面。二里头文化中晚期阶段,青铜器群的出现显得十分突兀,这又很难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寻找根源。二里头青铜冶铸业突然崛起,与外来青铜技术传入的关联关系研究,应当受到重视。
其次,是小麦的东传。中国北方传统上是粟类农作物种植区。至少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北方黄河中下游区域,突然开始种植小麦,并快速普及,改变了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的结构。人工栽培小麦的技术,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在西南亚,然后向四周传播。新疆罗布泊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以及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不迟于公元前2000年前,新疆天山地区古代居民已经广泛种植小麦。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中发现大量使用小麦进行祭祀的现象,反映出当年塔里木河绿洲区域麦浪滚滚的生态景观。中原地区突然夏代或略早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当由西方传入。另外,中原地区小麦普遍种植还引发更深层的学术问题。因为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由西方引进的小麦种植及相关的灌溉制度,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另外,除史前青铜之路和小麦种植技术外,羊、牛等一些家畜,是否也可能是随着青铜之路和小麦的东传进入到了黄河中下游区域。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三,器物交流的背后,反映的是人群的迁徙。1989年甲骨学家胡厚宣撰文认为,甲骨文提到的“土方”为夏民族。西域史学家余太山进一步说明,夏禹所统治的“土方”族群,实际上就是吐火罗人,他们曾生活在豫西和晋南。近年来,吐火罗人起源与迁徙问题是国际欧亚学界讨论的热点,欧美多数学者和中国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人原居地在黑海、里海以北的欧亚草原,吐火罗人的一支在夏代或更早的时候迁居天山,罗布泊小河墓地那些保存相当完好的呈现欧罗巴人种特征的人类干尸,为吐火罗人的遗骸。这里,如果胡厚宣论证的“土方”为夏民族可信;余太山所论禹治下的“土方”就是吐火罗不虚;小河干尸是吐火罗人遗骸之说也能成立。那么,吐火罗人为什么在夏代,突然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区域,他们是在什么背景下到的中原,它们的到来又对夏文明最终形成起到过什么作用?由此引发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讨论中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化,一些学术禁锢不断被突破。中原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外来因素的存在,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中原夏代吐火罗人的存在和来源问题,不应被束之高阁,或简单地视其为空穴来风、无稽之谈。这些都亟须从考古学、文献学、人种学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度梳理。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
- 推荐关键字:考古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济南发现汉代墓葬 画像石精美两方印章无印文(图)
- 2012-02-21
- ·地铁工地挖出南宋军用水壶或能验证岳飞驻军无锡(图)
- 2012-02-21
- ·陕西各类博物馆接待游客超过1200万人次
- 2012-02-21
- ·扬州瘦西湖考古发现琉璃瓦碎片
- 2012-02-21
- ·巴中平昌县发现悬棺葬
- 2012-02-21
- ·地铁2号线挖出宝 南宋“军用水壶”首次规模出土(图)
- 201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