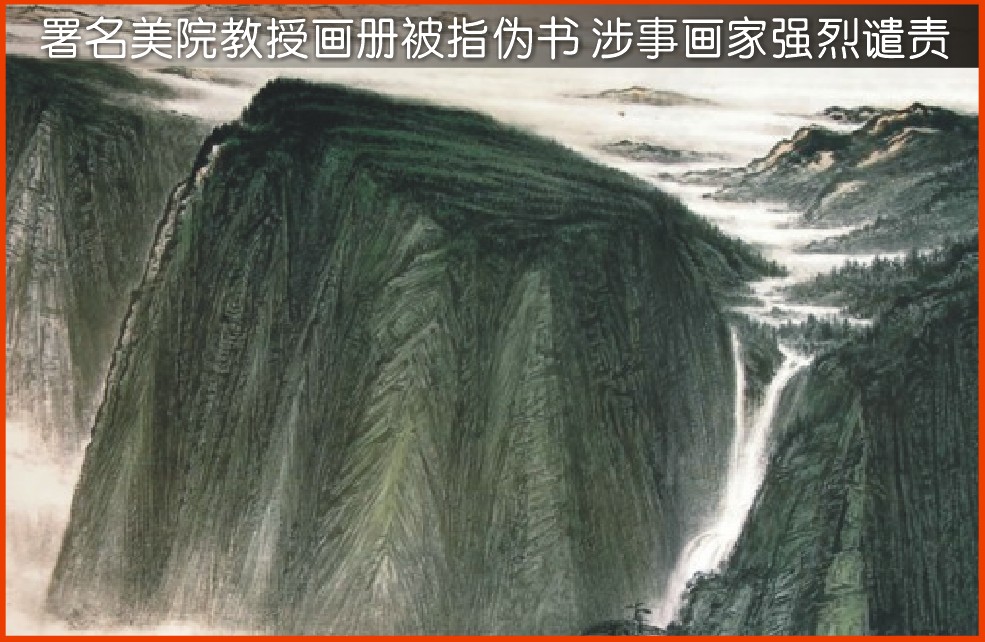张洹作品 孔子
看一些当代艺术展览时,脑袋里经常有个问题“蠢蠢欲动”:作者是谁?
字我认识几个,我知道谁拥有对作品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和阐释权等等一切权利,我不知道的是,那些用自己的双手把这些作品生产出来的人,他们是谁?谁打了这些明清家具,又是谁把它们拆开装好?谁编了这艘草船,谁造了这些箭?
张洹去年在上海的一个曾被批评为“犯傻与肤浅可笑”的展览,撇开内容不说,这些作品即是一种工厂化的集体创作。
记得去年在北京一家画廊举办的邱志杰展览《细胞》,用竹篾编成各种隐喻。蜂窝状单元是“细胞”,热水瓶凝固水柱化成树根是“灌注”,还有貌似望夫石的“凡是在时间中形成的都会在时间中消失”。这些土头土脑,摆放得活像考古现场的竹子软雕塑在邱志杰的作品系列里出现,应该说我首先感到了惊喜。首先是为这个雅驯统一的形式和样貌,竹子的温顺摇曳包裹、显形了各种隐喻、排比和他者的注视,完全是“文化的外衣”现出真身。
其次,继《贫困设计博物馆》之后,邱志杰把“文化考察”的群体性和项目感脱去,打造了这么一批回归个体创作的作品。尽管由于造型材料的限制,一律圆鼓鼓的像植物根茎,展览的边缘部分显得乏力乏味。但是,形体和六边底座之间的平滑衔接让我无法不啧啧称奇。谁编织了这些精巧的衔接?此刻我对工艺的好奇超过了一切。谁在乎谁写了雄辩的策划书,谁招聘来了合格的匠人,谁谈判出了展览场地和分成,谁的质量管理保证了展览如期进行, 此刻我只关心那个用灵巧的双手把艺术实现的人。
曾经这个问题是不需要问的,谁是艺术家就是谁造的,谁造的谁就是艺术家呗。直到1980年代打破了中国艺术家的童真。1982年,把波普艺术搞得很流行的罗伯特·劳申伯格来到中国, 带了十多个助手到了宣纸产地安徽泾县。他打算用宣纸做一批混合材料作品。宣纸工艺算国家机密,宣纸厂当然是外人免入。经中国美协领导调停,厂里派了老工人带着纸浆和工具住进县里宾馆。劳申伯格让他们做两种纸,一种特厚,一种薄到透明。然后又买来许多上海海报,剪下美女鲜花等他们觉得特中国的图像,贴到厚纸上再用薄纸蒙上。制作了50多幅作品,回美国,每幅卖了几万美元。待美方要向中方支付费用时,问中国人该怎么算。 安徽省外贸按照宣纸成本,每幅算了几十元人民币。署名权就更不用说了。造纸的工人和为作品篆刻的国家美协副主席师松龄都成了无名英雄—— local expert。
当代艺术,用多种媒介,现成材质,署名权都成为问题。尤其是作为公共艺术的计划,人多力量大,署名也迷糊。英国人安东尼·葛姆雷跑到广州郊区花县, 搞“亚洲土地”计划,请了440个当地居民用5天做了19.2万个只有眼睛的小泥人。虽然他的展览目录比劳申伯格在意识上到位一点,没有笼统称呼“当地人”,而是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写上去了。但是艺术成就只是算在他一个人名下的,不会算在这440中任何一人的名下。
艺术家越来越像是一个导演。他提出构思,拉来赞助,找来群众演员,最后对所有出品盖上质检过关的大印。美术史学家巫鸿在《张洹工作室:艺术与劳动》一书中也谈到,他发现很多作品都不是艺术家自己做的,而是依赖于工厂式的集体创作,因此涉及署名权的问题。
艺术家对此回应道,他有的项目是故意挑战署名权。 “那张《这不是一张自画像》的作品,我没有画过一笔。我自己的一张照片分成64份分给64个人用各种方法表现,他们也署上自己的名字,最后组成一张大画,署名还是我的。因为我对这个事件有署名权。”“最后关于署名权就是约定俗成的,在有些时代,只有师傅有署名权,徒弟帮师傅画画出卖署名权以换得受教育及生存的机会。我个人认为署名的动作没那么大快感,做出好东西的快感远远超过署名,所以署名权说所纠缠的权利和快感问题被历史扩大了。”
虚化署名权是一种有必要的策略。另一方面,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政治经济状况下,对署名权的讨论倒是实起来才好。当代艺术语境里,玩材料的氛围越来越浓。以前是亲自玩,尹秀珍玩裹布,宋冬玩水,徐冰玩纸和活字,不存在手脑分离。现在生产节奏加快,成功的艺术家逐渐从“玩材料的人”、从生产线上提拔成为“管玩材料的人”。他完全就是一个项目经理,负责运筹帷幄和内外交流,和“ART-手艺”脱离了关联,可是成品依然是以个人面目出现。劳申伯格和他的助手们之间还存在传统师徒间技艺呈递的关系, 拼贴是劳申伯格的本行。但是如果艺术家以其文化和经济特权凌驾于他并不在行的手艺, 完全依托手艺人的劳动但是荣耀归于艺术家。 手艺和手艺人在中国之不值钱,这可是接近于剥削了。
在架上作品的领域,文化资本家的产业链已逐渐成型并有了规模。成名画家雇佣一个班子, 一个星期内弄出四五幅几十平方米以上的画来做展览。“枪手画家”也成为产业。有个搞美术的朋友回国,立即就觉出亲自画画太辛苦,尽管还没有成名,一算价格,也觉得雇人给画很合适。作品是艺术家的孩子,如果做爱都由他人代劳,就算代劳的人没资格当作品的父母,可是作品还能算掛名人的孩子吗?
- 推荐关键字:当代艺术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艺术品市场春季调整哪些艺术品值得购藏
- 2012-02-06
- ·艺术品信托:投资顾问最要紧
- 2012-02-06
- ·日本当代艺术:抢先拿下奈良美智
- 2012-02-06
- ·西安美术馆将推出24场艺术家个展
- 2012-02-06
- ·龙年展望:艺术品投资回归收藏
- 2012-02-06
- ·第九届上海双年展主题公布
- 2012-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