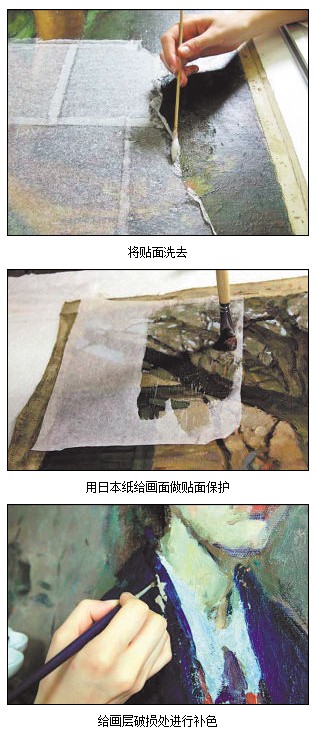从当代艺术的文化建构到资本市场的转向——以“艺术长沙”模式为例
http://www.socang.com 2011-12-27 16:14 来源:中国收藏网
目前,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偏离应有的先锋本质而朝向对金钱和权力膜拜。在名利场的带动下,由金钱和权力所形成的特殊场域不仅牵引着当代艺术发展的方向,而且还规定着艺术品呈现的形状。在资本市场引导下的当代艺术形态,最终去向是由展览馆走向拍卖大厅和收藏场所。而能够进入拍卖和收藏环节的艺术品则毫无例外受到资本的约束:在作品形态上迎合了被收藏和被消费的惯常标准。不仅作品的尺寸,而且是作品表现的方式和内容也大抵符合适宜销售的架上绘画的一贯特征。其实这是当代艺术愈来愈丧失其先锋特质,而走向庸俗化的征兆。
如果这只是当代艺术走向市场的初级阶段,那还无可厚非,毕竟艺术也需要资本的润泽。关键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今,连艺术被社会吸纳的方式都了无新意,赤裸裸地投向资本的怀抱,我们可以断言这些艺术及跨入富豪阶层的艺术家其实已无资格代表当代艺术的先锋性或前卫性特质,承担先锋艺术的探索性角色。而由艺术品市场带动起来的策展人、投资者、收藏者、艺术经纪人及画廊、展览馆、拍卖公司等当代艺术的相关机制,已经越来越注重艺术的资本特质和市场价值,而丧失对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的强调。尤其是各种类型的展览,无论是政府牵头,还是私人投资,都对艺术品的生成和确认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些现象从特殊的艺术体制中滋生而出,反过来又对当代艺术的走向形成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此种种现象,我们不能不正视其中的得与失,须谨慎看待这种现象背后所形成的艺术体制带来的实际效果和负面影响。
“艺术长沙”的展览模式提供了让我们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的鲜活范例。
“艺术长沙”已经举办了三届,均以私人投资的民营方式进行操作。2011年的第三届“艺术长沙”组织形式有了改进:政府开始支持性介入。虽然据称政府只是“给政策”而未投入实际的资金,但已是可喜的进步,表明当地政府开始有兴趣关注当代艺术。这次展览的组织和策划似乎无可挑剔。号称国际化操作模式下,由策展人圈定艺术家。由私人投资、政府介入及媒体高调宣传等方式,无不给当代艺术在中部省份的展示提供了便利,并增添载入历史的希望和可能。展览主题“解离”,按策展人吕澎的解释,具有宽松及包容性的意旨,从而给他选定的各类风格各异的参展人选铺平道路。但我们知道,无论是“解离”,还是“改造历史”及“溪山清远”,或者是其他什么主题,在以吕澎为代表的策展人看来其实展览概念并不重要。我们常看到的只是策展人对艺术现象和作品解读的错位和茫然,宏大主题和向传统讨资源等做法在当代艺术中比比皆是,毫不鲜见。展览主题表述的错位只是徒然加深艺术圈内理念的混乱而已,因为大多数展览理念并不构成展览的学术倾向性,只是一个促成展览顺利进行的由头。从1990年代初的“广州艺术双年展”开始,以吕澎为代表的批评家就介入商业运作。在以策展人为事实CEO的公司化运作模式下,策展理念毫无悬念地从应有的学术定位而演变成艺术资本化,后果必然成为对商业盈利的追逐,学术目的反而被旁置。但是,一个个具有学术建构意义的当代艺术展览背后如果是公司化的盈利模式和圈定的老面孔艺术家,结果只能是“学术”之词被抽空和滥用,真实内核却依旧虚空。近年来,国内日趋红火的艺术市场下,一帮名为批评家而实为艺术经纪人的当代艺术策展人依靠很多活动赚得金钵满盆,簇拥别墅豪车早已不鲜见,这在欧美发达国家亦非常见。相反,承担学术界定的那些真正有见地、有锐度、有针对性的美术批评早已成了稀罕之物。这一类以盈利为实际目的和操作范式的展览,丧失的是对学术精神的强调;耗竭的是稀缺的文化资源;泯灭的是当代艺术的草根精神;消解的是当代艺术的先锋性探求;隐遁的是展地当代艺术的可持续发展。至于以架上绘画为主的作品形态及一帮快过气的艺术家充当前卫形态的当代艺术,本身就欠缺前卫性的学理支持。倘若竟以此作为先锋艺术企望对展地民众做普及宣教工作,就不仅仅是缺失清醒的学术理解力和判断力,那几乎是迹近愚钝了。
“艺术长沙”的嘉年华模式在国内艺术展览中并不鲜见。但这次在具有娱乐精神的湖南得到了空前强化:时尚化、娱乐化、商业化及政府介入。其中时尚化是鲜丽的包装,给随后的商业收藏营造购买幻觉及提供信心保证;娱乐化是大众参与的外表,亦是展览形式的必须;政府介入是赢得官方支持的开始,并试图加强国家体制认同和政治合法性;而其中的商业化运作才是展览的根本目的,意味着资本市场介入艺术投资,并试图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赢得红利——不少展品被纷至沓来的收藏家收购及随后的收藏家年会的召开就是一个例证。作为参展人数有限的艺术家联展,这种方式在国内比比皆是,但是“艺术长沙”的操作却是一个成规模展览的规格,不能不说其商业操作和宣传推广是比较成功的。有力的策划和市场营销反过来强化了展览模式,最终也促进了参展作品的销售。这种策划模式在国内众多展览中具有一定标本意义。
应该讲,作为私人投资的艺术活动能做到如此程度已然不错,似乎又可宣称是一个数方共赢的圆满格局。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投资商为当代艺术的展示和推广无偿埋单而丝毫不考虑盈利,或者希望艺术家不去销售他们的作品。即便是展览所形成的所谓对当地的艺术普及功能和社会效应也不能完全被忽视。但是,凡此种种,都不应该是此次展览的初衷——无论销售业绩如何,盈利几分,毕竟这是一个有别于展销会的当代艺术展。而每个当代艺术展览后面理应被强调的仍然是展览的学术追求和文化意义,而不应是表面的娱乐喧嚣和实际的商业购藏。唯此对文化价值和艺术本质追求的强调,才是此类展览被纳入当代艺术范畴讨论的唯一意义,也是“艺术长沙”被命名为当代艺术展的前提所在。我更愿意提示的是这种展览模式后面的商业转向以及它实际的负面效果。我们深知,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取决于它的先锋特性,无论是对前卫艺术形态的探索,还是对它的人文精神的坚守,始终是指向艺术的文化内涵。在市场大潮下,当代艺术中的部分作品被收藏和盖棺定论是历史的必然。这既是对精神贡献的嘉许,亦是对那些苦苦追寻艺术本质、探索艺术新可能性的艺术家的一种物质褒奖。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当先锋艺术被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的那一刻,它的先锋意义实际上就已经终结。先锋艺术必须寻找它新的可能性,以便进一步拓展先锋艺术的表现疆域。当我们对当代艺术的精神企盼转移到对资本市场的追逐时,可以说当代艺术的先锋特性已然消失。剩下的只是收获它作为资本的物性特征和商业价值。这是作为精神营造和文化建设的当代艺术的宿命,亦是先锋艺术丧失它先锋特性的悖论所在。近些年国内高飙的拍卖价格不断撩拨着艺术家功利的神经,发财梦想早就迷幻了艺术家追求艺术的原动力,功利性的追求几乎成了艺术唯一的目的,艺术的人文建构和文化使命被模糊。在此过程中,作为展览发起的策展人几乎成了左右艺术家成功与否的救命稻草,而策展人作用的强大某种程度上就代表展览实际生成的学术走向和品质。当代艺术的先锋探索越来越被转换成朝向资本市场的商业运作。
必须承认,作为艺术活动的商业性操作,“艺术长沙”即便只能赢得开幕时的片刻辉煌,那也称得上是“成功”的。从展览运作到开幕,无论是八百嘉宾包机来湘,为使嘉宾车辆通过街头临时交通管制,以及模仿娱乐圈走秀美女相携走红地毯,当晚湘江橘子洲头夜放烟花等行为无不提示艺术嘉年华的媚俗特质。把当代艺术展览与政府活动及娱乐性一锅乱炖,说明策展人就没把它看作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展。而当代艺术的本质意义在于对艺术创造力的礼赞,决非制造新的权势并以新的特权来营造虚假的普世价值观来迎合盛世收藏的需要。从策展人遴选的艺术家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看得出是为了后续的作品购藏的需要。他们大多数属于成名的艺术家,作品相比他们以前并未有明显的突破。策展人是期待这些艺术家在市场上的号召力能够促成随后的作品销售,从而赢得商业性的成功。因为只有在商业操作中,这些颇具市场影响力的艺术家还存在一定的剩余价值。另外我们注意到,作为川籍的策展人吕澎,此次并未像前两次策展人那样视野多着落于湘籍艺术家,而尤为青睐大多数与他熟稔的西南片艺术家。我们看到,倘若策展思路中没有针对性的学术理念和宽泛的学术视野,人脉因素仍然是策展人选择艺术家的重要原因。这是为什么国内当代艺术展览频频,表面上热闹非凡,呈现圈子化和帮派化,实质上仍欠缺实际学术贡献的原因之一。
“艺术长沙”把时尚化和娱乐性引入当代艺术的操作中,也许是极富娱乐精神的湖南宣传方的一贯使然。但这种方式看似是一种无意识的宣传,实质上是经过精心打造的商业策划。让艺术家以明星的方式走秀,其实是以美化艺术家的方式营造当代艺术与大众的距离感,刻意提升当代艺术品的名贵性,凸显艺术品的商业品质。精心打造的开幕式极富营销策略,邀请了很多藏家参与,把当代艺术品的开幕办成产品发布会形式,目的并非为了宣传艺术的影响力而只是为了随后的营销活动。这种艺术发布会形式集中了现代产品营销活动的所有要素,即有产品(艺术品),有策划(走秀),有销售(订件),有卖方(艺术家),有买家(收藏家)。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场域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体制”。它强化了社会对艺术家的认知度,以时尚化的运作给艺术家以施魅,增加他们的当代艺术家身份的“圣坛效应”[1],以便于参展艺术家获得一种别样的身份认同。这种不以艺术品本身为中心,而以艺术体制为着重点的新型模式,实际上贯彻了丹托(Arthur C. Danto)在《艺术界》及迪基(George Dickie)在《何为艺术》等文中阐述的“艺术界”理论。艺术创作与欣赏再也不是单纯的审美关系,而是一整套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关系网络中创作、观念建构、评论、发售、欣赏、收藏等各节点”[2]形成了一个动态关系,而画廊、展览馆、博物馆、研究机构、批评家、收藏家、媒体等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体制[3]。新型的艺术体制对艺术的生成、界定和提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艺术体制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erre Bourdieu)所称的“文化场”的形成。而艺术品通过纳入这种新型的“艺术体制”,而超越了其单纯的“作品”意义,获得了新的解释和认同。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正是依赖这些新型的“艺术体制”而摆脱了原先对单一官办体制(官方的一套艺术模式,如美协及其举办下的全国美展给予艺术家的官方认同等)和艺术资源的依附而获得了自足的发展,从而获取了当代艺术可贵的话语权和文化场,例如,国内艺术界一些新兴大腕不经由官方体制而由新兴的艺术体制培育成为国内艺术界的翘楚等。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新型的艺术体制又逐步形成了新的权威性,从而影响和引导当代艺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新兴的体制进行认同和肯定从而强化艺术体制的作用。尤其是新兴体制中决定艺术家命运的攸关人——策展人和收藏家的青睐或忽视,而被入选重要展览或被金钱收购、拍卖等以获得独特的社会效应,并有可能被新型的艺术史所记载。这还不包括由于策展人的个人偏好或学术水准问题而导致的对艺术家的错乱遴选。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至少在国内,这种新兴艺术体制虽然偏离了官方体制的价值观(泛政治化)的束缚,但由于它天然的“软骨病”(缺乏有力的、较为系统和深度化的学术支援)和依赖性,而不得不转向以资本为导向的模式。这种新兴艺术体制缺点在于忽视了对艺术品本身及其价值的关注,而过度地倒向了社会民众被喧嚣的展览媒体宣传及评论家的美誉所形成的阐述场域,使艺术品被商业化,商业形式被体制化,艺术体制被权威化,从而滋生出“资本+权力”这个新的权力场。
“艺术长沙”的模式正是这种新兴艺术体制施魅的结果。它一方面摒弃了官方艺术体制的腐朽性和不足(以美协为代表的官方体制内展览),避免了被官僚性政绩化的官方价值观所整合,也避免了官方评选机制下评委们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情况的出现。这对当代艺术形成自立自足的话语系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艺术长沙”模式由于缺乏足够的学术判断和先锋意识,过度强化了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新兴艺术体制的影响力,从而给商业资本以充足的话语权。而代表资本市场的策展人、画廊、展览馆、收藏家等又形成了新的权力场,能够对艺术品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以便牵引当代艺术的关注点,左右它的发展方向。而国内真正有良知的批评家(不是那种既充当运动员的策展人又承担美饰和裁判功能的批评家)和专业媒体的失语,又使大众失去辨别艺术真伪与美丑的能力,使本应提升当代艺术层次及反馈于大众的文化资源被滥用,人文热情被挥霍,艺术未来的发展空间被提前透支。同时,又会使当代艺术不去承担先锋的责任,而把应有的担当消遁在商业化、时尚化及娱乐化中。在“艺术长沙”展览中,至少从现状和实际意义来看,明显可以感到展览并没有去寻找当代艺术中潜在的亮点和可能性,而堕入了庸俗化的商业循环系统中。“艺术长沙”作为在非中心城市举办的当代艺术展,本来完全有可能形成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不一样的艺术阐述模式。作为湖南这个地域也许可以利用当代社会中心逐步消解的大趋势,形成当代艺术的“异在阐述模式”,以另类的方法论阐释形成新的突破。因为在互联网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倘若我们有足够合理的思路和持续的实践,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艺术储备的非中心城市反而是有希望贡献出当代艺术新的可能。这些旨在提升当地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思路才是策展人主力去寻觅和构造的,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商业操作上,靠拉一些成名艺术家参展,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来营造出伪饰的盛世繁华。
面对众多当代艺术展览,人们没有理由只是看到它的商业操作,而忽视它在文化建构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负面作用。当前国内当代艺术展览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均超以往。各地均在打文化牌做展览,无论是成都艺术双年展,还是广州艺术三年展,抑或北京798艺术节,宋庄艺术节等,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展览只是资本(无论是民营还是官办)渴求下的喧嚣表面和大跃进式勃起的产物,与艺术实际的生产和创作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我们误判资本市场带给当代艺术的负面影响的话,就有可能高估艺术的实际成就而拔苗助长,致使艺术家创作心态失衡,并使已有的艺术生态失形。
卢卡奇(Gyorgy Lukacs)说过,艺术的责任是寻求再造社会整体的可能性。倘若我们不把市场和经济收益看那么重,我们就必须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承担起我们之于艺术史的那份责任,担负起艰苦的建构工作,不被“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资本市场所迷惑,从资本市场构建下的新兴艺术体制的视野中暂时脱离开来,着力关注艺术本体建构,寻找当代艺术新的前卫点和可能性。唯此,当代艺术才有实际突破的可能性,中国的当代艺术才能书写与它的时代密切相关的历史。
2011年9月25日于杭州
注释:
[1] 殷曼楟著《“艺术界”理论建构及其现代意义》,第23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2] 殷曼楟著《“艺术界”理论建构及其现代意义》,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3] 朱立元总主编、李钧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三卷),丹托《艺术界》,程介未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闻松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邹萍
- 推荐关键字:当代艺术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中国收藏网的立场,也不代表中国收藏网的价值判断。
相关新闻
- ·谨慎面对艺术基金热潮
- 2011-12-27
- ·在无极中闪亮——2011年徐阿森新作展即将开幕
- 2011-12-27
- ·北京永乐2012春季拍卖征集全面启动
- 2011-12-27
- ·杨劲松:关于水墨当代性的问答
- 2011-12-27
- ·贝伊勒:最成功的画商,最大胆的赌徒
- 2011-12-27
- ·盘点2011拍卖会“最贵”:齐白石作品4.255亿元(图)
- 2011-12-27
发表评论












![当代著名画家:张天武 [春风图]拍卖 -中国收藏网](http://image.socang.com/product/2011/09/14/L01344103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