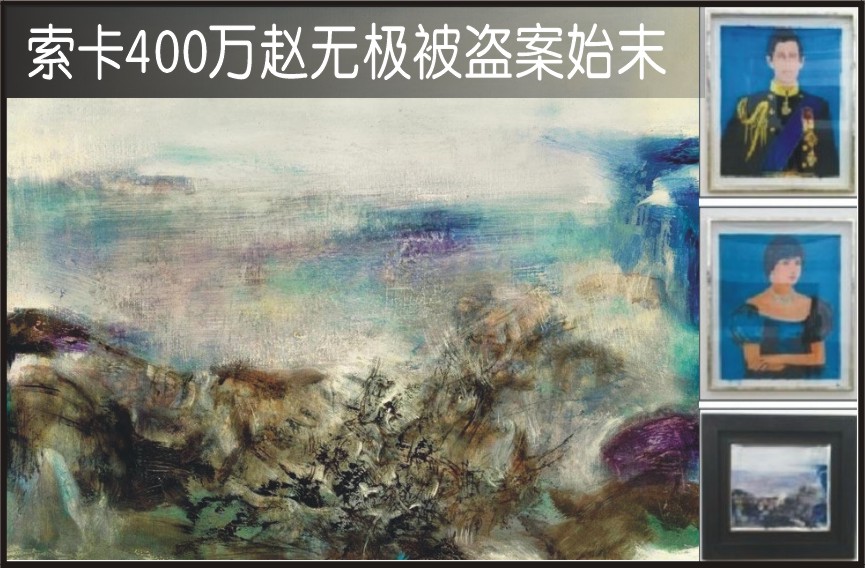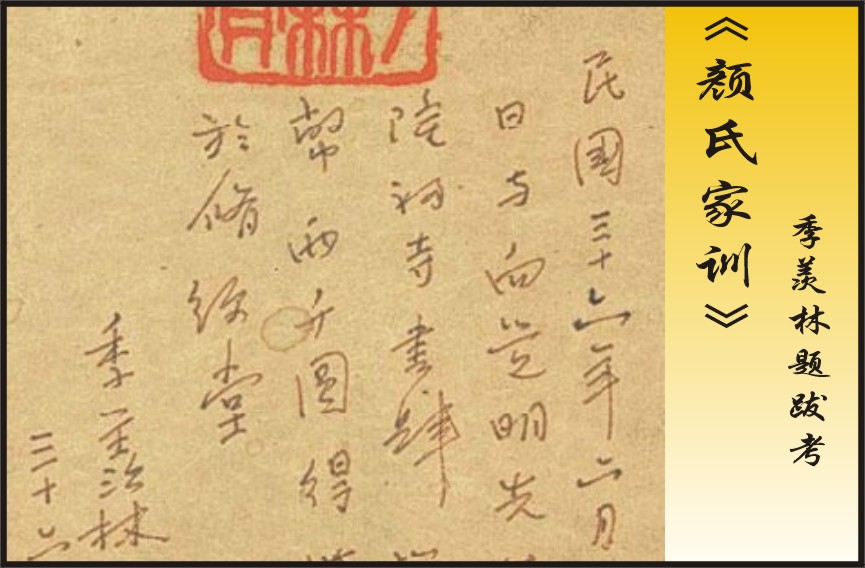记者:本届广州三年展围绕着美术馆的“拆”和“建”,延伸到城市化进程中的拆建问题,这个主题是如何从展览中体现出来的?
罗一平(以下简称“罗”):这届三年展用美术馆自身来提问,把美术馆的改扩建放到城市化的语境中,用“拆”和“建”作为关键词进行提问,即美术馆是什么、当代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拆”和“建”问题也突出了从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问题,以及城市现代化问题。展览的内部逻辑就是“拆”和“建”,整个三年展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在构筑,每件参展作品都在讲述着故事,整个展览像一本故事书那样上演着一部由乡村文化走向都市文化的大戏,我们从每个作品的选择到展品的陈列线索等等都反复在做推敲。
记者:本届三年展在展览结构和运作等方面,如何区别于其他双年展或者往届三年展?
罗:首先,这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跨3个年度的、由7个展览串成的整体展,分为启动展、项目展和主题展。以前的双三年展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很好的平台来探讨问题,我们想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用启动展来提出问题,再用3个项目展来把大的问题细化成子问题,深入剖析,总结归纳又回到大问题的回答,那就是明年9月份的主题展。
第二,我们开创了论坛模式,开展了行动论坛,分为广州站、纽约站和北京站,一共16到18场,邀请中国乃至全球著名的艺术理论家、艺术家和非艺术圈里的建筑学家、思想家和城市学家等进行对话和碰撞。
第三,这届三年展启动展里的艺术家不多,才40余人,基本上一个展厅里只有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问题意识非常强烈,也不热闹,能让人安静下来沉思,这是区别于其他三双年展,包括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地方。
记者:展览和论坛的数量这么多,费用的支出应该很庞大,美术馆在资金上有压力吗?
罗:政府在这届三年展中给予了广东美术馆前所未有的支持,用于论坛的80多万都是一次性拨款,后来又追加了200万,说明广东政府对文化的支持真正落到了实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企业的赞助,所以总体上而言,资金压力是有,但是不突出。
记者:过去您说过资本和美术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如果当资本和学术之间产生矛盾,美术馆的立场如何?
罗:美术馆肯定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广东美术馆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它能够在全球都产生影响,学术肯定是在第一位的。和各种资本打交道,是任何美术馆都面临的事情。引入资本的过程就是不断协商的过程,在协商的过程中我们自有学术主张,如果我们做不到,这块的资本我们就不要,这一年中我们拒绝了很多资本。
记者:那么对于本届三年展,美术馆、爱马仕品牌和艺术家冯峰三者之间发生的“学术与资本之争”的焦点事件中,美术馆有何回应?
罗:首先,爱马仕并不是本届三年展的赞助商,Hbox是我们的项目联盟,和邀请参展的艺术家不同,我们是收取了他们的展出场租的。冯峰知道Hbox项目是由爱马仕基金会赞助的,马上想象到美术馆有资本进入,构想了学术和资本斗争的场景,来和楼下的品牌产生冲突。当时他给了我一个方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A货现象进行批判,我们认为这个草案不错。但当最后一天来布展,把霓虹灯打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问题不对了。经过协商,艺术家同意拿下AI MA SHI当中的两个字母,使它拼不成“爱马仕”,还说把构成“爱马仕”商标嫌疑的装置也给拆除了。当然,爱马仕也来找过我们,出于我们对爱马仕的尊重,同时也是作为对文化的尊重,我们让艺术家更改。因为有爱马仕出面请我们来和冯峰协商,他就得到美术馆被资本操纵,在资本的压力下要求艺术家去更改作品的这样一个结论。
其实这时艺术家像堂吉诃德,对着风车这样一个假象斗争,显出他的某种神圣性。从艺术家自身,我认同他这个行为,但是从艺术的本体,我有两点不认同:第一,谩骂式的批判不是批判,批判要建立在学理性上,没有学理的批判没有学术价值;第二,是他的批判建立在一种假构性上,没有敌人,他在跟一个假想敌斗。我们给了他一封律师函,律师函不代表起诉,只是用法律的口吻来告诉你这件事超过了正常的艺术创作的度,希望改动。对我而言,我也是要维护艺术的尊严。
记者:三年展已经走到第四届,和其他展览比较起来,它有哪些不可代替的作用?
罗:三年展是一个大型展览,它所呈现的问题肯定是这个时期受关注的问题,起导向和整体呈现的作用。比如第一届三年展,第一次用官方美术馆来告知什么是当代艺术,正是第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十年回顾,在广东美术馆建立了十年当代艺术史。三年展具有的能量是一般的展览做不到的,他所聚集的知名艺术家和批评家是一般的展览不能比的,这就是三年展的味道。
记者:您对三双年展的未来有什么构想?
罗:三双年展肯定是在向前发展,因为这个社会会不断生产出优秀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批评家,在不同时期的策展人都会依据这个时期不同的社会需要、文化需要、审美需要等来归纳出这个时代的问题,三年展永远都会在问题的前沿上,价值还是有的,只是某一期可能做得好,或者不好,邀请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是否到位而已。
- 推荐关键字:美术馆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美国曾陷入债务危机的玫瑰博物馆开馆
- 2011-11-08
- ·南方最大私人博物馆落户凤凰山(图)
- 2011-11-08
- ·“天山南北”将首次全面展示新中国新疆题材美术(图)
- 2011-11-08
- ·王见的书法与绘画展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开展(图)
- 2011-11-07
- ·十位中国著名油画家绘写新东莞(图)
- 2011-11-07
- ·上海地区画廊缘何如此安静?(图)
- 2011-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