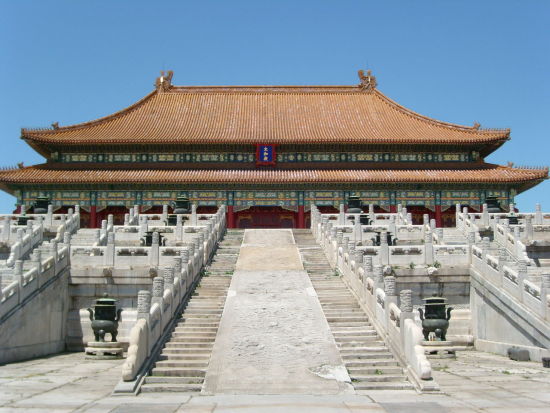纽约东村:波希米亚式乐园的覆亡
文/北回归线
这两栋楼起起落落的故事,并不遵循那种艺术家波希米亚式乐园的惯有发展线路,这里本没有抗争,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中国式维权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住户心甘情愿的选择。
纽约的西村与东村就像一对性格大相径庭的孪生兄弟。也被称为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西村,昔日云集了一批喜好纵横捭阖的知识分子、有头有脸的艺术家以及爵士乐好手,如今他们早已成了上流社会的精英,渐渐都搬离了“村子”,徒留下绵绵不绝的游人来此附庸逝去的风雅。而东村(East Village)昔日作为纽约朋克的根据地,为众多挤不进或租不起西村的落魄艺术家、音乐人、舞者提供暂时的栖身之所,那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它依然故我,不愿“改邪归正”。然而,改变终究还是不期然地姗姗来迟,东村最著名的两幢大楼——位于第一大街和第二大街交汇的十字路口的9号和11号。即将在爆破的轰鸣声中化作尘埃,与它们一同离去的,还有满墙的涂鸦、著名的火星酒吧和酒吧里“世界上最肮脏的厕所”,以及栖身其中不付房租也没有产权的租客。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摩登的新式大厦,整洁、明亮、便捷,没有记忆也没有负担。当然,最初的住户还是会返回这里,只不过他们的邻居不会再是一群穷得叮当响的艺术家,过去家园里的人与事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愈走愈远。
从都会荒原变为温馨家园
E.B。怀特在《这就是纽约》中写道:“纽约从来不缺慕名投奔的后生晚辈——青年演员、抱负不凡的年轻诗人、芭蕾舞女演员、画家、记者、歌手,每人都揣了自己的兴奋剂,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偶像。”Lou Reed、John Zorn、Patti Smith这些如今的元老巨擘都曾是寄居于东村的“后生晚辈”,而9号和11号就是与他们有着共同追求的人的王国。这些城市先锋自己动手将这片原本被人遗弃的都会荒原变成了温馨的家园。他们支付的房租极其低廉,有些甚至根本不用付房租,但他们并非毫无付出,坐享其成,他们为自己的小屋付出的是心血和时间,为这别人根本不愿驻足的破楼败宇注入了生命力。
在故事的最初,这里曾有两栋建筑。纽约市政府在1970年买下了这个街区所有房子的产权,包括9号和11号,当初计划在这里实施旧区改造,然而却迟迟未曾开工。
11号是栋3层楼高的房子,丝毫谈不上光鲜亮丽;它的邻居是9号,那是一栋5层楼的公寓房,同样也不怎么起眼。它们彼此相邻为伴,位于南北走向的第二大道靠西一边,休斯敦东街和东一街之间。它们的外墙已经斑驳凋零,很多户人家的窗户也不见踪影,擅自入住的流民和瘾君子搞得这里到处都是垃圾污水,脏乱不堪。然而,1976年,外外百老汇剧团(Off Off Broadway)的先驱艾伦•斯图尔特(Ellen Stewart)女士偶尔路过,毅然决定在此安一个家。她设法从政府手中租下了11号楼中的2楼和3楼。事实上,斯图尔特女士一手创建的剧团La MaMa Experimental Theater Club的大本营另有所在,她的固定住处也并非在11号楼,这里只是她度过周末的地方,没人知道这幢楼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了她。
艾伦•斯图尔特自己用了3楼一半地方作为工作间,另一半借给了当时替她的剧团工作的希腊雕塑师Athena Voliotis。2楼的一半给了搞剧社的同行John Vaccaro。他的剧社名叫Play-House of the Ridiculous,安迪•沃霍一手捧红的Taylor Mead、Ondine和Ultra Violet都曾在他的剧社中演出过。
这些新住户入伙后就开始了建设工作,运走垃圾,铺设电线,安装了锅炉和管道供暖,粉刷了天花板和墙面,不知从何处拉来了冰箱,修缮了楼梯。Voliotis女士花了好几个晚上把地板上烧焦的油布残骸清除。她把自己那半间房的墙壁刷成了白色,还安了个吊床,权当是治疗她对于故乡希腊的思念。Vaccaro每月支付的租金是294美元,从70年代末他搬进来直到现在,从没变过。
于是,11号楼里,一个小小的社区繁荣发展了起来。
1979年,斯图尔特女士把2楼剩下的一半借给了自己剧团的一位舞台监督格雷琴•格林(Gretchen Green)。那年格林女士34岁,她来自康涅狄克,当时正在办离婚。除夕夜,她带着3岁的女儿搬了进来,后来还养了条名叫Regis的长毛猎犬。她的这半个单元的形状不太规则,面积却不小,有220多平米,母女俩常常会穿上滑轮鞋,在屋里滑上好几个小时,一边还跟着唱机里Blondie的唱片歌唱。不过,这间屋子在冬天十分寒冷,孤儿寡母只好挂起塑料薄膜来阻隔渗入屋内的寒气,还得再放上好几个取暖器。
与11号楼的住客主要是艺术界人士不同,隔壁9号楼则是龙蛇杂处。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擅自入住的租客多是流民,但他们却并不这样看待自己,毕竟他们也在这里投入了他们有限的金钱、时间和汗水,他们视自己为这里的定居者。9号背后是著名的万国教堂(Church of All Nations)的所在,住户们一直习惯称他们的楼为7号半,因为再隔壁是7号,他们认为这幢楼其实更靠近休斯敦东街,但进口开在了第二大道上,于是才担了名不副实的9号。
80年代初,年轻的气功学生弗兰克•爱伦(Frank Allen)和一群朋友搬进了9号楼,在3楼开了武术馆。他们凿开了墙上的煤渣砖,开了玻璃窗,窗明几净的房间适合开馆收徒。
纽约的最后一片乐土
随着80年代的到来,9号楼和11号楼街区里的生活也有了点小变化。天黑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常常会在这里的人行道上烤火取暖,格林女士就趴在窗台上看着火光闪耀。她的屋子楼下的店面被一家搬家公司租了下来,里面有个员工是个酒鬼,时不时会把女人锁在店里。格林女士听见女性的嘶叫就会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只会过来把女子解救出来,却对附近停着的一辆人进人出的小货车视而不见。那是一家流动妓院,拉皮条的和妓女直接在里面接客。
不知从何时起,东一街成了毒品市场,格林女士从消防通道看出去,就能瞥见许多瘾君子躲在那里吸毒,烟头发出的火光星星点点,像是一片飞过的萤火虫。然而,格林从来就没有感到过不安全,“这里的邻里关系很亲切,”她说道,“虽然这里看上去很糟糕,但实际上你认识周围的每一个人。”比毒品更可怕的是艾滋病的阴霾,Vaccaro先生的好多朋友和剧团同事因此被夺走了生命。他对于戏剧的热情也随之一去不返。
好在新租客的到来为这两栋大楼带来了新的生机。
80年代中期,纽约皇后区的本地人汉克•彭扎(Hank Penza)在11号楼格林女士楼底下开了家名叫火星的酒吧(Mars Bar)。老顾客们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酒吧墙壁上,用涂鸦布满了天花板和四周墙壁,在号称“世界上最肮脏的厕所”里吸食海洛因。如果声音太吵,影响了女儿睡觉,格林女士就会打电话给彭扎先生,他会降低唱机的声音,然后叫顾客们闭嘴。
9号楼的墙面渐渐被涂鸦占领,旧的被新的覆盖,原来墙壁的颜色已丝毫不见踪影。武馆老师爱伦爱上了珠宝师拉娜•麦克阿瑟(Lana McArthur),他们带着几只猫眯一起搬进了9号楼武馆楼上的那间公寓。1991年,年轻的加拿大艺术家安德里亚•莱吉(Andrea Legge)搬进了9号的5楼,为的是这里房租便宜,她可以省下更多的钱用在艺术创作上。莱吉被这地方迷住了,在她眼中,这就像是个完全未曾被人发掘的国度,她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规划它的模样,探索各种可能性。于是,莱吉装上了玻璃窗,吊高了天花板,把工作室和卧室用一堵墙隔开。地下室里会有瘾君子过夜,他们离开后,莱吉就戴上厚厚的橡胶手套,穿上胶靴,把地上散落的针头和注射器收拾干净。异装双人表演小组合Kiki and Herb中的一员贾斯丁•邦德(Justin Bond)也带着一只名叫“珍珠”的小猫搬进了11号楼,住在格林女士的那半间屋子里。低廉的房租让自认为非男非女的她可以省下钱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出唱片和出书。
1999年,拉娜•麦克阿瑟因为乳癌去世。一年后,爱伦开始约会精通太极拳的蒂娜•张(Tina Zhang),后者在2001年8月搬进来与爱伦同住。他们一起教授中国武术,还有学生在这里举办婚礼。2005年,张女士赢得了全美太极拳比赛的女子冠军。
艺术遇上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为这个区域烙下强烈的个性标签,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叛逆者、艺术人士、乞丐来这里光顾,人越聚越多。虽然朱利亚尼当上市长后大力打击纽约的犯罪,但这里却似乎不受影响,反而还成了纽约的“最后一片乐土”。
原拆原回的艰难抉择
在9号楼和11号楼外,酒吧画廊和夜总会渐渐让路给了咖啡馆和小酒馆。9号的建筑情况越来越糟糕。莱吉看着从相连的其他建筑物上爬过来的腐烂慢慢侵蚀着她的外墙。她的排水管整整一年时间没有正常工作了,屋顶也漏了,墙壁上出现了之字形的裂纹,楼梯也开始摇摇晃晃。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开始对住户下达逐客令。虽然名义上住户是租住于此,但他们其实是不付房租的,因为房屋过去产权上的一系列问题,他们既不算是合法的宅地居住者,也不算是非法占据者,也正是靠着这种法律上的模棱两可,他们才能击退纽约市政府的清退令,继续住在那里,不用交付现金的房租,但是每月的维护开支都是大家一起出的。
2002年,一个旨在保护租户权益的组织“城市定居协助会”(Urban Homesteading Assistance Board, or UHAB。)以1美元的价格从市政府手里买下了9号楼,他们承诺会对它修护。和莱吉共享大厅的那位怪脾气的邻居当晚就搬了出去,拆除了所有他当初安装上去的设备,包括电线,那样也就没人能搬进来继续住下去了。市政府想把11号楼也卖了,但开价65万美元,住户们无力承担。于是,在其他住户的支持下,格林女士接触了BFC Partners,希望后者能帮助他们买下这栋楼。这是家专门建廉租房的公司,在纽约各处都有项目。作为开发商,他们有权拆除房屋内部设施,翻新或是全部拆除,只要能再建一栋新的并保护好老住户的权益就行。成功买下11号楼后,BFC Partners迟迟未开工,这让住户们既感到轻松,又时常提心吊胆。“我们都以为如今这事情很早以前就该发生了。”格林女士说。
在9号和11号附近的区域,旧区改造计划早已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东村的建筑格局慢慢发生了变化。9号楼后面的万国教堂所在的那栋楼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公寓大楼。莱吉渐渐习惯了变化带来的打击。当初那栋公寓大楼新建时,她很担心已经年代久远的9号楼会不会受到影响而坍塌下来,天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是身体状况也受到影响。结果证明她只是杞人忧天,那栋新楼还把朝着她后窗户的墙面刷成了白色,给她的公寓带来了更好的光线。“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莱吉说,“起初我很恐惧,但后来还是接受了现实,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原来那栋楼是什么样子了。”
在9号楼里,新东家许诺的修护工程始终没有兑现。按照他们某个员工的说法,部分原因是因为双方在经费上谈不拢。莱吉每天都为这栋楼的情况担惊受怕,甚至做了噩梦,梦见自己很老了还得为维护这栋楼而四处奔走,“我以为我只有那条路可走了”。11号楼的格林女士开始离开家,去佛罗里达看她的女儿和妹妹。每次回到纽约,她都感觉东村看上去变得更陌生了一点,“我走在邦德街上,感觉自己像是这座城市里最老最胖最穷的那个人”。
2008年,市政府对这一片重新分区,BFC得以借助政策便利,在11号楼的位置上建造一栋针对不同收入住户的建筑,市场化运作的同时保留一定数量的公寓给低收入人群,他们自己也能从中盈利。他们接触了UHAB,希望能买下9号楼,一起推倒重建。UHAB征求了住户们的意见,起先他们十分反感,不愿接受。但BFC同样许诺会给他们全新的公寓房一间,面积大小参照原住房基本不变,付出的只是不足挂齿的象征性费用,他们最终都答应了。
在9号和11号被拆除后,这里将建造起一栋12层的高楼,共有65个单元,计划在2013年完工。两栋楼里的9户人家被允许以10美元的象征性价格买下一间新单元,不过只能自住,再售出将受到严格的限制。此外,还会以低廉的价格向低收入人群出售4个单元,剩余的52个单元按照市场价出租,单间的价格在每月3200美元起。
这两栋楼起起落落的故事,并不遵循那种艺术家波希米亚式乐园的惯有发展线路——被市政府或是唯利是图的开发商扫地出门,也并非如知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微博里说的:美国“钉子户”靠着法律保护房客权益和州法规定贫富混居的条款拿到了廉价公寓。其实,这里本没有抗争,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中国式维权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住户心甘情愿的选择。他们固然舍不得让老楼就此灰飞烟灭,但长期为恶劣的居住条件所困、一直靠自己的绵薄之力辛苦做着大楼的日常维护让他们身心疲惫,经过了内心的苦苦挣扎,最后还是对开发商点了头。“我们都累了。”已经在这里住了20年的莱吉说。她为了把这里修成她理想的家和工作室,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心力。今年6月,她将被迫离开这里,等到2013年再回来。“大多数人都以为,届时我们可以免费回到这里,但我想请他们自己过来尝尝这里头的滋味。”
为了重聚的告别
过去差不多一年里,住户们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具体何时要搬出来。莱吉本以为是在去年9月,于是她都不怎么打扫家里了。火星酒吧的入口上方也早早挂出了标语:“Thanks for the memories”。
直到今年5月中旬,住户最终被告知,他们有两个月时间打包走人。在新楼建成前,他们每个月都能拿到开发商住房补贴,另借房子暂住。62岁的爱伦和他的伴侣张女士开始为武馆寻找新的场地;1980年以来,这家开在9号3楼的武馆已经教出了数千名学生,如今要离开了,“这地方有着别处无法替代的能量。”爱伦说。Voliotis女士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打包,睡眠也成了问题。火星酒吧的老板彭扎先生在搬离前的最后几天,还是一如往常每天下午拉把凳子坐在酒吧门口,边上放着个塑料杯,里面盛满了冰块和他最喜欢的威士忌。他告诉经过的朋友们,他会试着再找个新地方让火星酒吧重新开张,但很多人认为这话只是为了彼此安慰。在美国的点评网站上,感伤的留言铺天盖地,彭扎在7月22日留下了其中的最后一则:“朋友们,这一切都结束了。再见我的邻居们。历史上最叫人恶心的酒吧已经寿终正寝。结束了。”这两栋大楼里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住户艾伦•斯图尔特女士没有等到拆迁的这一天,她于今年1月13日去世,享年92岁,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纽约同志大游行的那个周末,异装表演家贾斯丁——他并非是最初的那批原住户,所以没能享受到将来的新公寓——在这里办了个大型的拆迁派对,这也是著名的第二大街11号楼的最后一场派对,人们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以后这里会变成另一副模样,充斥着来自郊区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开的店都是香蕉共和国和Gap这种。”特意过来参加派对的美术设计师Machine Dazzle遗憾地说,他身穿一件自制的紧身衣,脚蹬一双高跟鞋。
莱吉为了纪念自己在这里的日子,今年3月开了个博客,地址是“第二大街7号半”,博客的名字是“拆除前的纪念”。她的怀旧情绪肆意泛滥。就要离开居住了20年的地方,她依依不舍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我想要弄明白某些事情。”某天打包到一半时,她沉思起来,“这些事情都忙完后,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
格林女士给她的朋友们寄去了一封邮件。“写给每一个曾经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一起在这里画画、展览、派对、玩耍、工作、吃饭、喝酒、抽烟、玩闹、吸大麻等的人,是时候说再见了,向发生在这个了不起的地方的这段了不起的人生旅途说再见。”她写道,“但你记住了,我还会回来的。”或许将要回来的不仅有这些老东村人,还有东村特有的波西米亚精神。旧的乐园可以覆亡,只要精神不灭,新的乐园终将建起,如同怀特在《这就是纽约》中的结语:“这个怪异而又神奇的典范,如果抬头望去,消失不见,人将心如死灰。”
- 推荐关键字:纽约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艺术品市场表热里寒 可先从文化入手
- 2011-08-26
- ·肖像画的游戏规则变了(图)
- 2011-08-26
- ·国际金价暴跌10% 蓉城金饰变脸
- 2011-08-26
- ·大型意大利肖像绘画展亮相柏林伯德博物馆(图)
- 2011-08-26
- ·北京匡时九月赴美寻宝
- 2011-08-26
- ·意大利肖像艺术作品重要展览在德举办(图)
- 2011-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