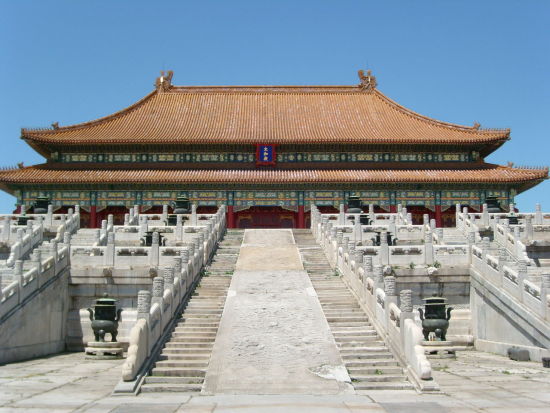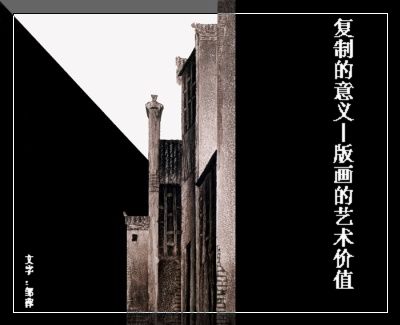自从当代艺术进入中国的美术学院教育,关于如何办学始终意见纷纷。有的学院旗帜鲜明主张严格管理,甚至希望规范课程和教材,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另一个极端则希望模仿西方学院,松散管理,用选修课和学分制作为课程的主要执行模式。两种意见本来各有道理,但因为都想消灭对方的观点,就开始互相批判和鄙视起来。
邱志杰/文
学院教育,可松可紧。严格管理如西点军校,或者韦尔斯利、史密斯学院之类常青藤女校固然人才辈出,松散自由如哈佛和伯克利照样也名震天下,原没必要就此打起笔墨官司。但自从当代艺术进入中国的美术学院教育,关于如何办学始终意见纷纷。有的学院旗帜鲜明主张严格管理,甚至希望规范课程和教材,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另一个极端则希望模仿西方学院,松散管理,用选修课和学分制作为课程的主要执行模式。两种意见本来各有道理,但因为都想消灭对方的观点,就开始互相批判和鄙视起来。
我曾经在英国和美国的美术学院短期上过课,他们那里的教授实在是很舒服。美术学院的教授,只要每个月参加一次硕士生的研究汇报会。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别的学生向做汇报演讲的学生提问质疑,老师则只是一个劲地在那儿说好呀好呀太好了,如果教授居然没有说你好,那你一定是糟糕得让他忍无可忍了。在这里课堂多数是讨论,平时学生自己折腾,到了东西做出来摆出来,教师才来听一听学生自己的解说,给点建议。学生要找导师见个面喝杯咖啡,先得提前几个月电子邮件预约。这些学院的情况,近于放养。我也在德语系统的学校上过课,气氛就很不一样。老师会在教室里面貌似很负责地指手划脚,某个教授的工作室,学生的风格基本也相似。我看博伊斯的传记,他和他工作室导师之间爱恨交集的,这种情绪,是典型的严父模式的产物。
放养的教育思路,其实受到艺术史上浪漫主义艺术观的影响。相信每个个体内部潜伏着天才,这种早就存在于学生那个体内的天才不宜受到他人影响的压制,教育的使命是让这种内在的天才不受阻碍地开放出来。学院只是提供一个条件,一种土壤,好的种子自然会生长起来,不要用严格的教育去拔苗助长。IT行业兴起之后,因为苹果、微软、甲骨文这些大公司的创始人都是退学英雄,这种放养的信念更加得势,并在中国国内获得了很大的影响。“不打孩子”、“在玩乐中学习”之类口号成了更进步的观念,大量具有强制训练色彩的教育策略被大量放弃。在台湾甚至兴办起了森林小学。而在大洋的另一段,中国“虎妈”的成就让美国家长瞠目结舌,开始反思自己的宽松教育让孩子丧失了竞争力。这种放养思路的另一个极端也的确不太争气,还真的相信艺术教育可以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中世纪行会模式,给放养的主张者很多批判的实例。
我总爱这么想问题:对立面的双方的差别可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对立面的双方一定是站在同一个地平面上,才有机会成为对立面。如果是不同台阶上的两个人,就对立不起来了。教育思想的背后是人性论。是放养还是需要强制,是其表现。目前位置关于人类天性的论述无非“性善论”、“性恶论”和“性空论”。但无论哪一种,大概都无法否认通过教育改变点什么。
实际上,即使主张学院要宽松放养的,也还不至于敢主张不要学院。按照浪漫主义的逻辑,即使已经是天才,没有合适的土壤和雨水也要夭折。放养论假定学生的个性事先已经丰满,或者学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理智地选择学习。但是一定是存在着各种妨碍他/她最终获得成就的不利因素,需要通过教育来排除这些不利因素。这种教育是明心见性,帮助学习者寻找自我。但还是需要教育来做点什么的。放养论的反面,假定学生在学习之初并不具备已经完整的个性,也并不具备选择能力,只是一张白纸,因此需要输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他最终通过学习获得自我。这也是要求教育做点什么。甚至于更极端的性恶论者,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教育压制不良倾向,引导到正途上来。于是采取强制的手段硬性教育和规训。这一派就更主张教育的必要性了。
只要承认教育有必要,差别就没有那么大。只是环境不同,对象不同,目标不同,阶段不同,必须采用不同办法而已。
通常教育的外部环境较好,教育单位的管理就相应地可以比较宽松。这就好比一个孩子生长在音乐之乡的音乐世家,满大家都是吹拉弹唱的音乐人,即使父母亲不天天逼着小朋友练琴,小朋友有心无心地总能唱上几句,学起来也快。如果外部环境很恶劣,就不得不施行严格管理。比如满大街娼寮妓院,寺庙为了让人清修,就不得不弄出三规五戒。戒律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修行者和恶劣环境相对隔绝,在较为清净的环境中成长。所以,教育的宽松实在和环境有关。英美一些国家博物馆、美术馆系统和媒体都较为发达,良好的教育资源比较平均地分配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层面,美术学院只是整个艺术教育中的一个环节,采取较为放养的方式就完全可以理解。
教育对象不同,自然方式也就不一样。如果学生即使不来上你的学,基本生存保证也不受根本性的影响,来就读艺术学院,只是为了寻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宽松的放养就比较可行。如果学生来上学,是渴望通过学习获得生存技能,从而能确保自己的职业前途。那么即使你想要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鼓励他们在宽松的情况下自修为主,恐怕学生也不答应。别说他们缴了学费,就要求获得物有所值的教育产品,就算国家公费的义务教育,也有时间成本的问题。另一方面,学生心理越成熟,就可以越宽松自由,如果学生是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有问题的未成年状态,宽松放养的自修就比较难于推行。国外的美术学院,职业技能教育的成分更低,真的有不少是生存无忧之后的纯理想主义的梦想追寻者。有的是已经成年的人在美术学院寻求生活乐趣,甚至有成熟的艺术家为自己创造安静的反思环境而来读研究生。我在英国就遇见过七十几岁的硕士研究生,在美国遇见过这种著名艺术家学生。这样的学生,你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当他们的“虎妈”了。
教育的阶段总是一张一弛交替的。前面说到的外部环境,其实就是提前帮助美术学院做好了前期教育。基础较好,因此一进来就可以宽松。如果没有前期的良好准备,就不得不严格。等到基本素养习得的阶段结束,要求教育的成果的时候,自然要求课程必须是对症下药的,甚至,要求课程有连续性,高度精密,必须长期地进入才会获得结果。这时候就很难让学生和老师都处在凭感觉的状态。这也好比体育锻炼,你只是处在要把身体炼好,追求的只是身体健康,那么什么运动项目都接触一下总是好的,你也就比较可以凭兴趣来选择。但是一旦你是希望能参加某一个项目的比赛,你就不得不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严格训练。
当然, 大众寻求健康的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是有关联的,通常前者水平越高,竞技成绩也就越好。所以,我们也要看到,学生的成熟程度和教育模式也是互相塑造的。我们的教育如果永远是保姆式的,学生们当然也永远成熟不起来。这还真有点像孩子学走路,你永远不敢放手,孩子就永远学不会自己走路。可是你也不能一开始就不护着扶着,眼看着小孩摔死呀。
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模式应该宽松还是严格,首先是要去问一问学生们。教学体制的设计者不要凭着自己的信念想象学生的需求,并展开无谓的争吵。到学生们和家长中发放一些问卷,到可能的用人单位发放一些问卷,作一点调查,应该能得到比较靠谱的依据。毕竟,为教育买单的是他们。
以中国的艺术教育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我们的学院应该不可能是单一模式的。我们的社会需求中,职业技能训练的诉求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但是也开始有更高的需求出现。是否不同的学院应该明确自己不同的定位?或者在一家学院之中,就应该有不同的定位层级?因此,考验我们的政治智慧的,就绝不是在不同的想法之间分出谁对谁错,而是要找到一个让不同的想法能够兼容的方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当代艺术教育才刚刚开始,我们还不能肯定什么模式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因此应该允许更长时间甚至永远的摸索和实验。
所以我一方面对于急于规范教程和统一教材的冲动心存怀疑。对于我们目前这个阶段,不是要求同存异,而是要“存同求异”,尽可能多地尝试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我对于直接搬用某些欧美院校的放养论也不敢苟同。实际上,国外的名牌学校总是在高度自由的选修和学分制之外,另有一个手段来确保放养模式下学院教育的成材率,那就是高淘汰制。学生当然可以完全自由地选修学分,也可以休学出去混几年再回来接着读。学腻了不学了也没关系,反正你学费一年一年地交着就可以了。你要最终拿到毕业证书,就得拿出硬功夫来打出十八铜人阵才让出山。这种高淘汰率下,学院方面和教授尽管宽松好了,学生们自然哭着喊着要你多管管他们。我倒是很希望我们的学院能模仿这种方式,可惜现实是,我们连末位淘汰制都做不到。基本上,能考进来的,不出意外都能拿到学位走人。这就像一家没有质检部门的工厂,这种情况下,过度地把赌注押在学生自觉学习的成熟程度和自学能力,学院的品牌就有点风险了。
基本上我是个“性空论”者。但是今天的学生在来到学院大门之内的时候,已经不是空空如也的了。他们总是已经带着一些什么了。其中有已经准备的很好,只是需要你帮助他自学的;也有不灌输点什么进去就真的一无所有的;甚至偶尔还有已经满脑子习气不严加管教实在不行的。理论上应该因材施教,该放养的放养该严管的严管。但实际上时间成本不允许个个都因材施教。因此放养其实反而成了精英教育,对基础好的学生有效。严管成了起码的职业教育,是对于后进学生负责。实际操作中,只能用两段制,对于很可能更多地必须满足职业生存需要的本科教育后期更倾向于严格,对于培养精英艺术家的而且我们能控制招生质量的硕士生,更多地放养。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中国,甚至在别的国家也一样,学院除了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教育产品之外,本身还负有学术使命。就算学生和家长全都只是想来美术学院中花钱玩耍四年,学院也不见的就应该办成俱乐部。而且,学习的过程本身会改变学习的目标,一开始想要混个文凭玩耍几年就回家帮助老爸老妈照顾生意的,也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诱发浓烈的兴趣甚至历史责任感,决心不管不顾地走艺术家道路。一开始心雄万里的少年意气,也可能随着现实磨损成混口饭吃的平常心。因此我们必须假设,如果学生并无远志,他在这里能得到的是基本的教养和合格的知识。而只要他有更高的追求,向上走的台阶就总是敞开着。 学院的服务对象,也不仅仅是这些眼前看得见的学生和家长,同时还要对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负责,要对一个文化传统的未来发展负责。越是伟大的学院就越是承担着这种学术使命。也就是说,学院归根到底还是要有理想的,要用这种理想来感召青年,形成一个理想共同体。理想和精神不是依靠强硬的灌输,而是靠它本身的魅力来吸附参与者。有了这种理想的存在,严格的训练就不是压抑,而自由也不是飘荡。 学生来到学院的时候,一方面已经他拥有了自由。我们的教育绝不仅仅是对他重申他的自由而已。他来到学院不仅是为了知道这一点,这一点他其实已经知道了。而在另一方面,除了这种不受压制和强迫的自由,他其实还可以更加自由,那就是,学生应该有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帮助的自由,在学院中获得理想的自由。
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当口,2011年4月30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教育大会”上,本文涉及的问题果然再次爆发。这一次,争论发生在中央美院的两位教师吕胜中和展望之间。吕老师总所周知地坚持教学要严格规矩,强烈主张规范统一教材的也是他。展望在演讲中发表了了一通放养论。于是两个人互相讥讽起来。于是我从听众席中举手发言如下:
我们要警惕两极化的思维习惯和被对立面绑架的假批判性。
比如在历次教学研讨上都会出现的关于学生个性放纵到什么程度,教程是否要严格和规范等等问题的争论。比如刚才展望和老吕的略带火药味道的小调情。其实,双方的分歧可能没有各自以为的那么大。只是每个执教者所处的不同位置,有时候是被迫选择一种对立立场来表达而已。有时候这种不同,甚至只是同一个执教者面对不同对象,处在不同教学周期的可以理解的选择。比如,就教程是否要规范的问题: 教学要不要追求质量?要追求质量的话,从一开始不太知道怎么去教就比较随意地去教,到后来比较心中有数了,难免渐渐科学和严格起来,于是就有可能形成模式。形成模式有好有危险,好处在于有个批判的起点,成为理性反思和进一步修正的基础,甚至于作为学生的反叛对象,都是有其价值的。它的危险也很明显,那就是沦为教条,甚至于公式化,口诀化,成为禁锢思想本身的东西。这不是实验艺术独有的问题,所有的人类建构都存在着教条化的危险。
要解决这样一个两难,只能是尽可能多地发明模式,提供选择机会。因此,保留差别就变的特别重要。我不觉得要"求同存异",而是更倾向于要“存同求异”。差别存在,就不怕教条,教条就有机会由坏事变好事。也就是说,学院有机会成为成为产生学派的地方。
因此,我们要爱我们的差别胜过爱我们的共性。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与我们有所不同的方式的存在是我们免于腐败的机会。即使在一家学院内部,如果有可能,也最好形成这样一种张力。学生之间的相互教育,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相互教育,才是最重要的。能够形成共同体,相互给予意见的前提,恰恰不是相同,而是差别。柏拉图的学院模式即使不是真的,也是一个好理想。
此外我们要意识到,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设计完美的教学构架,千秋万代的完美学院。学院的使命都是历史性的。其实一个学院在特定时代能够完成伟大的使命,就已经很成功了。像包豪斯,或者黑山学院,或者约瑟夫博伊斯的杜塞尔多夫。
在进入学院体制之前,所谓实验艺术实际上也处在一种体制中,甚至有所谓“混地下的”,反体制的体制。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不断地自我批判。特别是,提醒一种临时性和历史性。只要记住一切建构都是临时的,它的危害就总是可以忍受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学院对自由的保护能力。在学院之外,我们并不自由。甚至于在最形而下的层面上,学院也是学生们最不用考虑卖画的时候,在他离开学院之后,他其实就再也无法自由和浪费了。在一些方面我们确实已经拥有不用把钢琴弹得像莫扎特那么好的自由,但是把钢琴弹成那样对我来说更是一种自由。
- 推荐关键字:艺术教育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收藏艺术品应按不同的需要层次购买
- 2011-08-24
- ·小汉斯:巴塞尔将瑞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展览(图)
- 2011-08-23
- ·关于艺术基础教学改革的相关问题
- 2011-08-23
- ·文化部官员:将推出四项措施支持动漫产业发展(图)
- 2011-08-23
- ·专家支招艺术品收藏:按不同的需要层次去选择
- 2011-08-23
- ·太平洋2011金秋艺术品拍卖会拍前综述(图)
- 2011-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