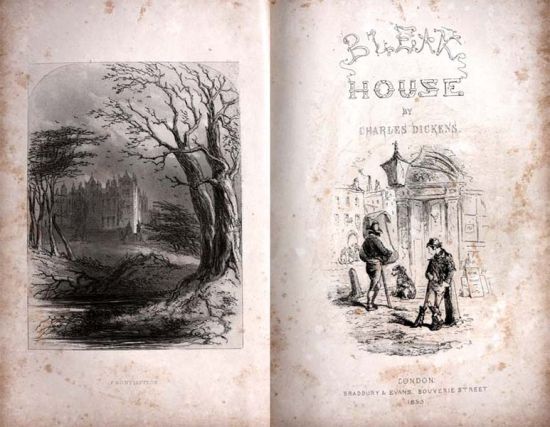-
①钱运达(右)与柯明在研究人物造型

-
②片中老太爷掉进了聚宝盆,变出了一堆老太爷

-
③《天书奇谭》中的狐狸精
“甜芦粟”钱运达动画作品中的幽默感
老老夏
现在的读者也许对“钱运达”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不会不知道《草原英雄小姐妹》、《天书奇谭》、《女娲补天》、《邋遢大王奇遇记》、《白雪公主与青蛙王子》这些动画片吧?它们正是钱运达的作品。
钱运达先生在圈内有个绰号——“甜芦粟”(一种植物,又被称为“高粱甘蔗”),意为他说话“啰嗦”。既然啰嗦为什么要加个“甜”字呢?这就意味着大家很喜欢他,因为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使得他的“啰嗦”带上了甜味;更可贵的是,这种幽默感渗透到了他的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有人说:《天书奇谭》可以说是我国的动画片甚至包括故事片里最有幽默感的。
在捷克学到了什么
1929年出生的钱运达本来是学绘画创作的,25岁的时候成为中国唯一被“公派”去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动画的留学生。勤于思考的钱运达觉得,一直在美术学院“纸上谈兵”,与美术片的生产实际有些脱离,起了回国的念头。正在这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特伟带着一个代表团访捷,担任翻译的钱运达就问他,学成之后回国干什么呢?美术设计,还是导演?特伟态度很明确,做美术设计没必要来捷克学习,我们的美术片有自己的绘画艺术特色,一定要学导演,全面掌握整个动画片的创作流程,包括一些新观念、新手法。
作为交流,特伟带去一部他自己导演的《骄傲的将军》,这部片子民族特色鲜明,技术上也比较成熟,放映结束时,全体起立鼓掌。捷克人说:“钱运达不需要在这里学了,回去吧,你们能搞出这样的片子,还到我们这里来学干啥?”
这是玩笑话,也是捷克专家对中国动画片的由衷赞美,但当时捷克的动画片水平在国际上非常先进,整体上还是比中国强得多,像《好兵帅克》、《鼹鼠的故事》等等都相当出色,所以在艺术观念和艺术手法上还是大有可借鉴之处。于是,在特伟的努力下,钱运达之后的学习安排有了调整:上午去电影厂学习,下午回学校完成各种理论课程,晚上有时候还要去电影厂加班实习。钱运达来回奔波于学校和电影厂之间,好在两处离得很近,分别在伏尔达瓦河的两岸,5分钟的路程。
地处欧洲中部的捷克是个小国,经济上、文化上经常遭到周边大国的控制,这促使他们对别国的文化扩张有着强烈的抵触,而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特性,无论绘画、动画、音乐还是电影,都如此。幽默无疑是捷克人民族性格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特点,他们不喜欢说话一本正经的人,钱运达的幽默感便理所当然地在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发扬光大,捷克老师也非常喜欢这位“甜芦粟”中国学生,在他学了5年半后要回国之际,友好地赠言:“希望早早看到你的片子,并且希望在你的片子里看不到‘捷克味道’。”
这句话让钱运达记了一辈子,成为他日后创作时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像捷克人那样,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不能有太多的洋味,方式方法可以洋,味道决不能洋。与此同时,还要努力在民族和现代两种文化形态中寻找交叉点,既要在民族文化的根基上汲取营养,又必须加上现代的审美观念,在老古董的基础上有所翻新,这是钱运达这一代中国动画艺术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部合拍片的夭折
1959年回到上海美影厂后,钱运达拍了多部出色的美术片,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与万古蟾合导的剪纸片《金色的海螺》,1964年曾获印度尼西亚第三届亚非国际电影节卢蒙巴奖。还有《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钱运达骨子里已经浸透了自己和捷克人的幽默,所以连《红军桥》这样的红色作品也受到了批判,因为他把这么严肃的题材也拍得滑稽。
1980年代初,英国BBC提供了一个剧本,说是中国的神话故事,要与上海美影厂合拍动画片,由他们投资。可是剧本写得乱七八糟,从盘古开天地到《山海经》,还有其他传说、神话故事,什么都有,角色繁多,线索杂乱。美影厂便向英国BBC提出,合拍可以,我方负责重写剧本,否则就拉倒。
编剧的重任落到了王树忱和包蕾身上,他们从原剧本写到的一大堆情节中,发现了《平妖传》里的狐狸精故事,大概占了整个篇幅的10%。
《平妖传》最早是罗贯中编写的中国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二十回,后经冯梦龙增补改编,成为明末以来通行的四十回本。《平妖传》在中国古典神话小说中也不算很成功,但里面的几个人物很有趣。王树忱和包蕾就保留了三个狐狸精,把担子和尚改成了小孩“蛋生”,海阔天空地重新创作了剧本,很多有趣的情节几乎都可以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找到:
天宫“秘书阁”执事袁公趁玉帝赴瑶池聚会之际私取天书下凡,将天书文字刻在云梦山白云洞的石壁上,因此触犯了天条,被罚终身看守石壁天书。一天,袁公踏云巡山路遇蛋生,为将天书传于人间,嘱蛋生等白云洞口香炉升起彩烟时拓下天书。蛋生遵嘱照办,又经袁公指点勤学苦练,运用天书为民造福除害,治蝗救灾。狐狸精恨蛋生妨碍其作恶,耍阴谋窃去天书,勾结官府,继续祸害百姓。蛋生与狐狸精多次斗法,争夺天书时,袁公到来,收回天书,并用白色石镜将狐狸精压死在云梦山下。袁公自料难逃天庭法网,嘱蛋生把天书文字记在心里,然后用一把神火将天书烧尽。霎时雷电交加,玉帝圣旨下达,将袁公擒归天庭问罪……
蛋生在剧中是善的代表,狐狸精是恶的代表。蛋生与狐狸精的冲突是明线,而袁公与玉帝之间的矛盾则是暗线,都分别具有象征意义。英国人觉得,重写的剧本的确比原来的好。可是,半年、一年、一年半,BBC的资金始终没有到位,而创作程序已经启动,先是王树忱、包蕾,再是钱运达……美影厂只好自己拍,把原先“太出格”的戏收回来一点,以符合国情,但无处不在的幽默感还是“存了盘”。于是,一部合拍片就此夭折,却由此诞生了一部从指导思想到创作方式都有别于其他中国美术片的“邪门”动画作品,这就是《天书奇谭》。
有趣是动画的生命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从事动画片创作的艺术家们就一直对“美术片的特性”这一话题争论不休。阿达说:动画嘛,动的画,画的动;有人说是“想入非非的艺术”;搞理论的总结为:夸张性、假定性,极度的夸张、极度的假定;曾当过《解放日报》国际版主编的编剧谢天傲则概括为三个字:奇、趣、美——情节、动作、造型都要奇,也要有趣,而且有审美价值。大家都在琢磨,片子里会有多少噱头,多长时间让人笑一笑。而钱运达记得捷克的老师说过,“要理解我们捷克人,可以去看《好兵帅克》。好兵帅克是一个聪明的傻瓜,我们只能做傻瓜,因为我们太弱,老是受欺负,但我们其实在用傻瓜的方式玩你们。”
创作《天书奇谭》,以王树忱和钱运达为首的创作班底都不甘心做成一部只给小孩看的电影,尚方宝剑就是特伟老厂长提出的八个字:老少咸宜,雅俗共赏。
主题思想:惩恶扬善。对老百姓好就是善,坑害老百姓就是恶,这个道理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特地设计了一个极其低能的小皇帝,下面有一级级贪财、好色、仗势欺人的官吏,是想说明,拥有权力的无德无能者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祸害。
主题思想确定之后,他们的宗旨就是怎么有趣怎么玩,玩到极致。贪,就用贪来惩罚他;色,就让他因此而丢性命。王树忱本是个冷面滑稽,冷不丁会冒出两句话令人喷饭,所以和“甜芦粟”钱运达一拍即合,聊着聊着就乐。
为了使人物造型更具有独特性,钱运达请来曾与他合作过《红军桥》和《张飞审瓜》的南京《新华日报》美术编辑柯明(原名吴樾人)担任设计。柯明把潜心研究的中国民间的艺术、绘画、雕塑、玩具、戏曲这些元素全用到艺术造型上。《天书奇谭》中的很多角色形象来自于戏曲造型,生旦净末丑俱全,如狐女的斜眼、两片腮红,是吸取了京剧旦角脸谱的造型艺术特点;县令是借鉴了丑角形象,加上非常夸张地采用削尖的鼠脸和鼠须来加强他的委琐感。特别好玩的还有小皇帝的造型,就像那种用硬纸板做的、很土很便宜的小玩具,脖子是一根细木棍,硕大的头可以自由转动。
这些都为动作设计提供了最大的发挥余地,可以根据每个人物的造型特点、性格以及在戏里的规定情节来设计动作。比如那个太监来宣布:“宣狐女进宫。”他的嘴形就是长的、扁的、圆的不停地在动。那个小皇帝因为圆滚滚的看不见脚,走路就像不倒翁一样一摇一摆。蛋生吃饼先吃掉中间,再套在脖子上,转着圈吃,透出一种机灵劲。知府小眼睛不停地转,转得越快坏心眼就越多,同时配有“咔咔咔咔”的响声,像一对骰子发出的声音,充分表现了他的诡异与狡诈。
配音也是怎么有趣怎么配,比如曹雷说“我要好多好多的鸟儿”——舌头一卷,拖音很长,为小皇帝增色不少。
《天书奇谭》完全脱离了那个时代尚流行的塑造“高大全”人物形象的轨道,处处发散出幽默感。钱运达说:有趣是生命,一部动画片要让人看得下去,每个环节都要有趣,从编剧、导演、造型设计到最后的配音,都很关键。大家做加法,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
- 推荐关键字:动画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漫画收藏也成气候 丰子恺作品最引人注目
- 2011-07-21
- ·3D动画片恐怕“幼儿不宜” 动漫人主张慎用技术
- 2011-07-21
- ·小人书渐成大珍品(图)
- 2011-07-21
-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调查
- 2011-07-19
- ·25岁铁杆“刚丝”18年收藏变形金刚400多个(图)
- 2011-07-15
- ·“十二五”动漫产业新风向:沉下心来弄精品
- 2011-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