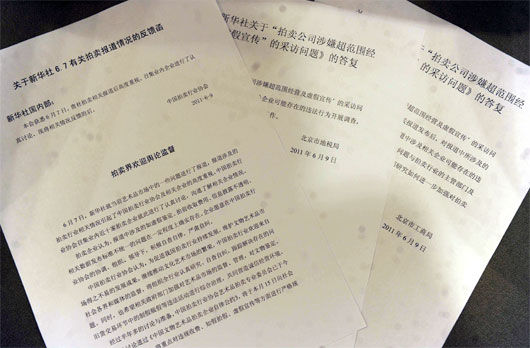位于柏林米特区的Kunsthaus Tacheles

Support Tacheles
文/韦伊
Kunsthaus Tacheles一部分像是艺术家的殖民地,一部分又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但无疑它是最最柏林的。经过了20年的物换星移,这里仍然是柏林艺术创造的温床。然而,这一切究竟还能幸存多久,如今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虽然位于柏林米特区的Kunsthaus Tacheles(Art House Tacheles)不太出现在各类旅游指南上,但艺术爱好者拜访柏林时决不会漏掉这一站。它一部分像是艺术家的殖民地,一部分又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但无疑它是最最柏林的。它的饱受创伤的外墙上画着巨大的壁画,投射着难有答案的人生课题——HOW LONG IS NOW,金属雕塑从门口一直延伸到了马路上,楼梯边画满了一层又一层的涂鸦和壁画,很多已经完全无法分辨,互相层层叠叠。经过了20年的物换星移,这里仍然是柏林艺术创造的温床,一楼开了一家酒吧、一家咖啡馆和一家电影院,楼上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他们在那里展出自己的作品,还有音乐家把那里当成排练室,然而,这一切究竟还能幸存多久,如今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1908年,16岁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正在等级制森严的凯撒·弗里德里希学校备受煎熬,以至于他可能无心顾及柏林城内增添了一座宏伟的拱廊式建筑。这座融合了早期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和哥特风格的五层建筑的精美度无法与他日后醉心的18世纪的巴黎拱廊街相提并论,或许因此他才没有在《柏林纪事》以及别的文章中为它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记录,但这座建筑的落成在当时的柏林也算盛事一桩。从1907年开工到1908年落成,整个工程花费了15个月,由当时供职于帝国建筑办公室的著名建筑师Franz Ahrens亲自督建。整栋建筑物超过9000平方米,横跨弗里德里希大街和Oranienburger大街,通过拱廊通道将两条大街连成一体。它是当时柏林第二大规模的拱廊建筑,建设费用花去了将近700万德国马克。
借着普法战争胜利的东风,德国经济迅速崛起,私营业者尤其是犹太商人在从事生产之余渐渐有了闲钱进行投资。Kunsthaus Tacheles最初便是由这群人联合投资建成的,他们想实验各家店铺分别售货,然后统一付款,也就是具有大超市雏形的销售模式。可惜才经营了半年,就宣告破产,它变成了按传统模式经营的百货公司。1914年,一战爆发前人心惶惶,它再次被公开拍卖;1924年,大楼开始改建,挖了很深的地下室,层高也大大降低,完全改变了之前的面貌;1928年,通用公司在此建成了展示厅;1930年代早期,纳粹上台后征用了这座建筑,它变成了“德国工人前线”和党卫军的办公室。1943年,这栋建筑进入了它最暗无天日的时期,作为关押法国战俘的监狱,它的天窗部分都被封了起来;后来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纳粹淹没了第二地下室,直至今日那里还位于水面以下。
Kunsthaus Tacheles一部分像是艺术家的殖民地,一部分又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但无疑它是最最柏林的。经过了20年的物换星移,这里仍然是柏林艺术创造的温床。然而,这一切究竟还能幸存多久,如今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虽然位于柏林米特区的Kunsthaus Tacheles(Art House Tacheles)不太出现在各类旅游指南上,但艺术爱好者拜访柏林时决不会漏掉这一站。它一部分像是艺术家的殖民地,一部分又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但无疑它是最最柏林的。它的饱受创伤的外墙上画着巨大的壁画,投射着难有答案的人生课题——HOW LONG IS NOW,金属雕塑从门口一直延伸到了马路上,楼梯边画满了一层又一层的涂鸦和壁画,很多已经完全无法分辨,互相层层叠叠。经过了20年的物换星移,这里仍然是柏林艺术创造的温床,一楼开了一家酒吧、一家咖啡馆和一家电影院,楼上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他们在那里展出自己的作品,还有音乐家把那里当成排练室,然而,这一切究竟还能幸存多久,如今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1908年,16岁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正在等级制森严的凯撒·弗里德里希学校备受煎熬,以至于他可能无心顾及柏林城内增添了一座宏伟的拱廊式建筑。这座融合了早期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和哥特风格的五层建筑的精美度无法与他日后醉心的18世纪的巴黎拱廊街相提并论,或许因此他才没有在《柏林纪事》以及别的文章中为它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记录,但这座建筑的落成在当时的柏林也算盛事一桩。从1907年开工到1908年落成,整个工程花费了15个月,由当时供职于帝国建筑办公室的著名建筑师Franz Ahrens亲自督建。整栋建筑物超过9000平方米,横跨弗里德里希大街和Oranienburger大街,通过拱廊通道将两条大街连成一体。它是当时柏林第二大规模的拱廊建筑,建设费用花去了将近700万德国马克。
借着普法战争胜利的东风,德国经济迅速崛起,私营业者尤其是犹太商人在从事生产之余渐渐有了闲钱进行投资。Kunsthaus Tacheles最初便是由这群人联合投资建成的,他们想实验各家店铺分别售货,然后统一付款,也就是具有大超市雏形的销售模式。可惜才经营了半年,就宣告破产,它变成了按传统模式经营的百货公司。1914年,一战爆发前人心惶惶,它再次被公开拍卖;1924年,大楼开始改建,挖了很深的地下室,层高也大大降低,完全改变了之前的面貌;1928年,通用公司在此建成了展示厅;1930年代早期,纳粹上台后征用了这座建筑,它变成了“德国工人前线”和党卫军的办公室。1943年,这栋建筑进入了它最暗无天日的时期,作为关押法国战俘的监狱,它的天窗部分都被封了起来;后来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纳粹淹没了第二地下室,直至今日那里还位于水面以下。
1948年,这栋饱受兵燹的建筑被移交给东德自由德国商贸联盟(FDGB),多家零售商和制造商临时以这座废墟为大本营,还有一家名为“Camera”的电影院也在此开张,地下室则归东德的军队使用。1977年,政府在进行了一次工程评估后,决定把它夷为平地,打通两条大街。工程在1980年开始陆续进行,拱廊中间的大穹顶被拆除了,电影院也关门大吉。
然而,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它的命运。1990年2月13日,距离原东德政府计划彻底推倒它还剩两个月,名为Künstlerinitative Tacheles的艺术小组占据了这里,他们说服政府重新评估建筑物的结构整体性。令人意外的是,它的情况远比看上去要好,甚至获颁历史地标性建筑。获得重生的它有了一个新名字——Kunsthaus Tacheles。Tacheles在意第绪语中的意思是直言不讳(straight talking),意在向它最初的用途致敬。知名策展人Jochen Sandig在此为艺术家提供住宿和工作场所,早期进驻的艺术家包括Mark Divo、雕塑家团体Mutoid Waste Company、音乐创作团体Spiral Tribe、DNTT剧团、表演艺术家Lennie Lee、舞蹈家Sasha Waltz等。
电影《再见,列宁》以柏林墙倒塌后不久为故事背景,导演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er)曾透露影片一场戏的灵感正来自Tacheles。“那真是一段非常自由的时期。”奥地利出生的媒介艺术家Martin Reiter常常回忆起1990年代那段最好的时光,尽管最早的那批艺术家或因为功成名就,或因为一事无成纷纷离开,但Reiter依旧选择了留下,现在他成了Kunsthaus Tacheles的发言人。整个1990年代,新柏林吸引了无数的金钱注入和旅游客流,米特区也成了泡沫式发展的核心之一,房地产投机风靡一时。在Tacheles里,出现了两个矛盾对立的利益团体,一个是不为盈利的艺术家团体,另一个由实业家组成,他们看中的是这里超低的经营维护费用,靠给底层舞厅的舞客卖啤酒而大发横财。由于历史原因,Tacheles的产权关系相当复杂,直到1990年代末期,德国政府才最终厘清,并将它交给了投资商Fundus Group,他们许诺为包括Tacheles在内的这块地方做一个好的发展计划。在详细计划出炉之前,他们允许艺术家们继续呆在这里,只要支付象征性的0.5马克的租金。1997年,HSH Nordbank与Fundus Group产生借贷关系,因为后者还不出钱,银行成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而艺术家们的租约也在2008年到期了。
今年4月初,那群实业家组成的团体——他们占据的多是作为商业用途的底楼和后院的部分——以1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手里的这部分。之后,底楼的很多店面就关门了,还竖立起一堵新的水泥墙,可能是为了防止新人入驻,也可能是为了让剩下的那些人感到不方便而主动搬出去。新东家据说有个宏大的发展计划,他们要将这里变成柏林的苏荷区,建立奢侈品旗舰店、豪华宾馆等,计划随时可能启动。
59岁的德国艺术家Volker Witte在二楼拥有自己的工作室,虽然他没有什么名气,也不指望将来会有名气,但他很满意眼下的生活,“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出现在这里,会来到我的工作室,和我一起谈论艺术,偶尔还会买点作品,让我能够继续创作下去。如果我被告知,自己将被踢出这里,那真是巨大的打击。”柏林文化部门很希望这块地方能保留下来,但早在2007年“拯救柏林墙”运动时,这个负债超过600亿欧元的政府就表示爱莫能助,如今更无法为Tacheles提供多少帮助。好在艺术家从来都不是好惹的,Martin Reiter现在就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为保留Tacheles而斗争上,“我大量写信,用一种所谓的艺术的方式,想要去改变我们面前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但是,他也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我也想将保卫Tacheles之战变成一场游击战,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堡垒,我们正被人包围。我期待着看到有一天,那些银行家和律师们站在外头的人行道上,挥舞着手里的纸板,嚷嚷着‘艺术家滚出去’的口号。”
- 推荐关键字:“艺术区”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从贸易商到当代艺术赞助人(图)
- 2011-06-10
- ·当代艺术重在贴近百姓才不会是瞎胡闹
- 2011-06-10
- ·段 君:当代艺术与市民无关?
- 2011-06-10
- ·当代艺术展孬画不孬 意在摆脱束缚(图)
- 2011-06-09
- ·万众瞩目:达莎·朱可娃(图)
- 2011-06-09
- ·“孬画”不孬 意在摆脱束缚
- 2011-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