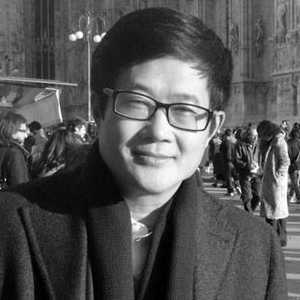
吕澎
——关于成都双年展主题展《溪山清远》的历史和思想起因的说明
———————————————————————————————————————
终于要离开了,不是因为正在离开的过去让人生厌,而是生命有一种抓住未来并将她变成让人回忆的过去的力量。
———————————————————————————————————————
开始了,需要十个月完成的又一个征程——成都双年展。
就在上周,当接到市委宣传部发来的关于2011年成都双年展的工作通知,我知道了,无论愿不愿意,我都必须在未来的十个月里尽可能以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这届成都双年展的工作。此时,5月开幕的“改造历史”展览的《“改造历史”工作汇编》的编辑工作还没有结束,校对还在进行,设计还在进行,可是,一个新的大型展览的工作就要全面展开。
很多人熟悉“成都双年展”,他们知道这是成都企业家邓鸿从2001年开始赞助的一个连续性的展览。可是,这次,成都政府决定整合政府与民间的更多资源,举办一个由不同操作机构参与完成的不同主题和形式的数个展览构成的“成都双年展”。我负责成都双年展的整体策划以及主题展《溪山清远》的策划。
我当然知道,人们习惯了一个个双年展的不断举办,并且有了太多的厌倦。不过,我没有精力去分析别人的厌倦,我已经被每天交替去从事的工作——写作、教学、参加活动、讲演、会议以及数个展览的准备——压得没有一丝时间去关心别的问题,我就像一个在行驶中的火车的司机,紧张得只能关注前方,而难以环顾路过的一个个美丽的景点。
我不是那种非常逻辑地分析与排列问题的人,所以,我依据最近的感受,很断然地将这届成都双年展的主题展定名为“溪山清远”。这个题目是我2004年的博士论文使用过的题目,那时,我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在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上。选择这个方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洞见,而是一次补课。我属于缺乏丝毫传统知识训练、缺乏充分历史知识积累的那代人,直至1977年底进入四川师范学院报到之日,我阅读过的书屈指可数,西方图书只读过塞万提斯的《唐·吉科德》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书仅限于《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小说。可以想象,进入大学之后,这代人才逐渐有了机会阅读中西方的图书,知识才开始有了积累。这足以印证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在传统知识领域是如何地欠缺,以至当面临许多问题时,总是长时间地缺乏成熟的判断。例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中的很多人会这样判断: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建设的阶段,古人那些坐穷悠壑、冥思苦想而成的图像传统怎么可以在今天继续下去?与今天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当人类的科技手段足以创造全新的图像时,我们怎么能够将一幅王石谷的笔墨营造的淡泊来呼应呢?我有很长的一个时间里同意这类判断。可是,如果我们对历史给予细细地思量和考察,会发现,不是物理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相反,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经历,我们曾经被要求相信的教条,蒙住了我们思想的眼睛。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教导的结果,而是一个被思想、权力、制度所强制灌输的结果。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的传统精神是被另一种野蛮但有效的力量给摧残至深的。
“五四”时期虽然有“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声音,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用武力和制度去强迫人们去改变他们的文化信仰,在很多时间与机会里,那些从欧洲回来的激进艺术家仍然舞弄着手中的笔墨在宣纸上作画,而那些坚持传统精神的“守旧”者仍然有条件保持着他们“古旧的”优雅,让世界的人们目睹另一种文明的风格与精彩。直至1949年,关于现代化或者西画的讨论并没有影响人们对风尚与习惯的选择,如果推翻满清政府之后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没有遭到战争的干扰,如果那些开始新社会的人们对民主宪政有更清晰的了解和筹备,一个混杂着不同历史时期而多样的中国将是何等地精彩。2008年我参加张晓刚在布拉格的美术展览时,看到和听到的故事让我们更加深信这个道理:这个城市的人民在法西斯即将攻占布拉格时,选择的是投降,以便保护他们的历史与传统。他们采取了一个更加符合民族精神的方法和态度,他们将屈辱埋藏在心里,他们相信会有重新收回这个城市的那一天。这个城市的一切——无论是什么——都被保护了下来,他们没有因为阶级与民族的仇恨而毁灭自己的历史与文化。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民的永久纪念,我坐在共产主义博物馆里,独自一人观看1968年的春天苏军坦克进入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录片,流下了泪水。然而,那些让人联想到血腥和残暴的物证却依然被放置在博物馆里,所有参观的人们可以从这些物证中看到那年春天发生的惨烈的故事、看到悲壮的过去,所有的历史物证都成为今天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财富。
我们的传统在1949年之后被以不同的名义给受到批判和“扬弃”。知识界熟悉关于“精华”与“糟粕”、“传统”与“创新”区分的教导与指示,而事实上,对那段历史有经历的人知道,所有的知识只有在是否符合特定的政治目的的前提下才成其为知识,否则只能作为“毒草”而被清除——焚烧、拆毁、砸烂。直到1976年,“香花”与“毒草”都属于两个威胁到每个艺术家肉体与政治生命的意识形态词汇,在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那里是缺乏这样的背景知识的,经历者的回忆,在很多人那里至多不过是一种夸张的历史说辞。不过,他们的确应该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他们——70、80年代出生的人——对传统知识的缺乏与无知,不是因为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导致的,不是因为高科技带来的手段与新工具革除的,相反,是意识形态批判及其相应的制度铲除的结果。传统的文化与精神被消灭得如此地没有栖身之地,以至在不少年轻的批评家那里很自然地将那些星星点点恢复的笔墨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这样看,对于人类的文化来说,残酷的还不是物理上的消灭,而是精神上的漠视。今天,人们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图书,可是,如何重新认识和复兴我们的文明,却完全没有展开——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教育导致的漠视的结果。
我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我清楚80年代的艺术资源来自现代主义的革命;我们经历过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后现代的碎片——思想和语言形式上的——直到新世纪还是很多艺术家的资源。这些主要来自另一个文明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开启了中国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在提醒人的自觉和独立,并要求人们关心通过民主宪政来实现真正的自由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80、90年代针对专制主义、本质主义的艺术实验开辟了艺术创造的新天地,尽管体制仍然约束着新艺术的发展,但至少,在思想与判断的独立性上,中国艺术家获得了多种文明的武器。
从今天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工作陆陆续续开始了。有很多不同年龄的当代艺术家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认识到了一种背景力量的存在与恢复。
我在几年前就在何森的工作室里看到了他对古代绘画的重新理解;在上海MOCA的一次展览会上,我看到曹敬平借用传统的绘画方法对油画的实验;我一次次地在周春芽的工作室里翻阅那些涉及古人的画册;在欧洲国家的旅途上,看到张晓刚在翻阅《左传》;在朋友的口中,听说方力钧在收藏那些古人的绘画;在常州或者在路上,我与洪磊经常给我讲述关于江南和园林的故事;在曾梵志的院子里,看到了不少从江浙一带买来的石头与墩子;在江南一带城市的游历中,我看到和了解到不少年轻的画家在继续使用宣纸与毛笔,尝试着接续被断开数十年的传统笔墨,他们借用着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洗礼的方法与视角,完成了让人不可忽视的新国画,……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在不同的城市里,四处能看到人们对传统文化和趣味的恢复与沿用。
不要去怀疑艺术家对传统的恢复与沿用仅仅限于模仿与抄袭,一个接受活生生的灵魂指挥的文化不可能是一层不变、重现过去的面貌的。要相信心灵的自由将成为一种溶剂,将艺术家所获得的所有知识与感受融为一种新的艺术面貌。有天赋的艺术家会带着尊重的态度以及敏感性去接续而不是重复传统,其中只有一个是不变的,知道吗?那就是气质。
每一种文明都有她特殊的气质是别的文明没有的。我们可以在字典里找到太多描述我们的传统的气质的术语,例如“超然”、“澹泊”、“高逸”或者“凄美”之类的……等等等等,但是,只有当我们面临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那些属于我们自身传统的气质究竟是什么。只有不断的领会人生与这个世界,修为的高低就会在我们的言行中见出。而在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乃与使者驰而问豫且曰:“今昔汝渔何得?”豫且曰:“夜半时举网得龟。”
《史记·龟策列传》里的这个“今昔”指的是“昨天晚上”。时间并不久,它甚至都不是昨天白天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长度很能够说明中国今天的新艺术与她昨天之间的距离。其实,艺术家们之间的工作是重重叠叠的,我们说的转变就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只有更具敏感性的艺术家才能够把今天早上的和昨天晚上的风景区分开来。有人睡眼朦胧,可是他聪明的话,他会看到庭院里刚刚发出的新芽,他会去培养和帮助她的成长。
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欧阳文忠公集·相州昼锦堂纪》里的“今昔”指的是“现在与过去”。好了,从艺术史来说,对过去依依不舍的心情应该放置下来,我们要一段新的历史成就。我在伦敦的时候,有好几个国外的朋友在谈到中国当代艺术时都使用了“疲倦”这个词汇,我是明白的,那是针对过去了的、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当代艺术。现在,既然心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不应该创造新的当代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昔”的距离已经遥远。
“溪山清远”仅仅是一个提示,只要有一点中国文化的常识,谁都知道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即使对于那些与中国文化有历史渊源的国家的艺术家来说,也不是难事。我想将那些心中拥有同样感受的艺术家的工作集中起来,举办一个展览,让更多的人看到:无论这个世界是如何地复杂和充满问题,我们需要精神上的洗礼,需要重新反省自己的文明,从那些有文明修养的古人思想里寻求可以转换的滋养。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精神的下降状态总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尽管这种状态有它的理由;可是,我们将如何来安排精神必要的上升?4月在旧金山举办的展览,我将继续使用这个标题,直至9月的成都双年展的主题展,我还是使用“溪山清远”,我想通过重复的提示,来说明我对正在处于明显变化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我想鼓励这个变化,并参与到艺术家对这个变化中的问题给予解决的艺术工作中去。
自然,我很难保证展览将有什么特别的奇迹会发生,我仅仅是将一种新的倾向给予强调并告诉给观众和艺术家: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也许应该参与到对这个倾向的关注和实践中。同时,我极力要避免那种通过智力游戏和思想手淫来表达当代艺术的存在和意义的方式,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思想是缺乏物理社会能够给予呼应的思想;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游戏是无目的的游戏。因为,有价值的思想永远针对现实;无目的性仅仅是古老的哲学欺骗。“溪山清远”不过是让我们大家回到一种清新的思想与艺术实践的状态中,具有牺牲精神地建设新的文化大厦,不管社会现实有多么的残忍,而日常个人问题又多么的深重。
2010年11月14日星期日
- 推荐关键字:“展览”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美院“喊”大家去看毕业展(图)
- 2011-06-02
- ·冉劲松作品陈列展·馆藏作品展(图)
- 2011-06-02
- ·香港很专业 内地要努力
- 2011-06-02
- ·还有多少国宝隔海相望
- 2011-06-02
- ·“易·常——梦务”崔载锡展
- 2011-06-02
- ·1.9亿是否就是张大千价格顶峰
- 2011-0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