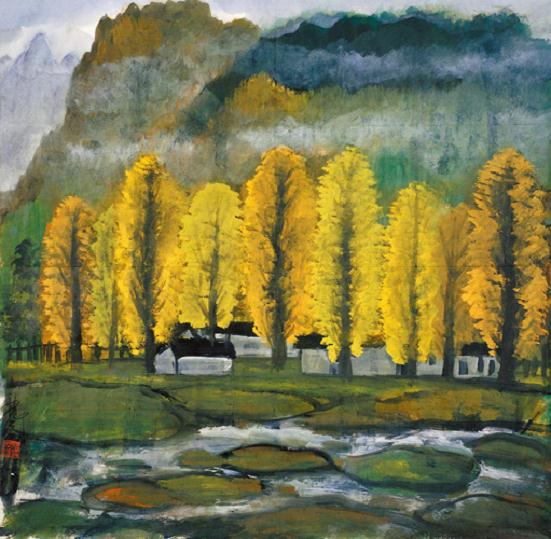Katharina Fritsch, Stilleben (《静物》), 2011, 威尼斯双年展作品效果图。
准备回归:名为“ILLUMInations”(illumination意为“发光”,nation意为“国家”)的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6月1日开幕)昭示着对启蒙运动(甚至文艺复兴)教义的历史性和审美性回归。策展人比奇·库莱格(Bice Curiger,苏黎世美术馆馆长、《Parkett》杂志联合创办人,曾经策划过众多大型展览,如“扩展的视域”[the Expanded Eye]等)将通过82位当代艺术家和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大师丁托列托的三幅作品回顾明晰、知识、政治和视觉等经典概念。《艺术论坛》主编郭逸安对库莱格进行了采访,访谈内容涉及到即将召开的本届双年展,以及它在世界范围内对西方现代性的重新审视。
郭逸安(以下简称“郭”):本届双年展的名称“ILLUMInations”除了影射启蒙运动之外,似乎还涉及到沟通传达的方式,以及传递失误、民族语言及其翻译和误读的问题。
比奇·库莱格(以下简称“BC”):完全正确。我想出了“ILLUMInations”这个标题,然后仔细想,“哦,你疯了。”但是在同一个词里添加多重含义又有何不好。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光”的意思,那当然就成了一个经典的艺术主题,这样不仅有点枯燥,而且太抽象。通过强调那个莫须有的后缀,这个词具有了一种更加现实的依据,一种不同的语义。
郭:而且这个提法让我们想到了启蒙运动和现代性,总而言之就是关于个体与集体、国家与世界的问题。
BC: 对,我看过尼古拉斯·波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的一本书叫《茎上根》(The Radicant, 2009),这本书恰好就涉及到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要么你有一种全球化的混合腔调,说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要么你就得开始协商(negotiate):你要保留的价值观是什么,什么样的价值观更值得保留。也就是说,启蒙运动和理性的观念化一直以来都受到攻击。但如果你思考人权,那么显然,这种现代的传统还是值得为止奋斗的。这些价值依旧值得弘扬。
郭:15年来,很多国际性的展览似乎都试图想发表关于全球化或者多元民族化的声明,而往往陷入对经济全球化的简单批判,要么就陷入人类大家庭的幼稚观念。你的构想是什么, 回到启蒙的理想,避免后者的陷阱?
BC: 对于这个问题,我更想从艺术谈起,而不是上来就谈一大堆文化理论,或者社会学,政治话语之类的东西。双年展正是一个谈艺术的好地方,因为不管怎样历史和政治都是唱主角的。那些对双年展大谈世界理论的人会说建立各个国家馆是这个时代错误。可问题是,就算你抹去场所记忆,你依然会犯这个错误。
郭:你这次挑选的很多艺术家在其艺术创作中都反映了作为一种已然现象的区域问题,就像你说的,国家馆项目中暗含的东西那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如果说对于民主化的重新发现是整个世界的一种诉求,那么你策划这次展览是否涉及到中东的骚动,或者说得更大一些,涉及到对国家和城市未来安定的迷茫?
BC:有一个意大利艺术家,叫Norma Jeane,他的作品就触及了埃及革命的问题。他的东西不错,要知道,参加这次展览的一共有82位艺术家,我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东西出现。
郭:而且你布置了接纳这些偶然性的临时场所,比如艺术家Franz West、Oscar Tuazon、 Monika Sosnowska和宋冬的作品。
BC: 我管它们叫“parapavilion”。在国家主题馆之外,这些“parapavilion”是一个另外的空间,其中艺术家们(例如Oscar)可以制作容纳其他艺术家作品的雕塑。
然后我们邀请Asier Mendizabal在Oscar的作品中展出作品,因为Mendizabal的投影幻灯作品在军械库(Arsenale)这样的地方很容易被忽视。Franz West的馆很有意思,当我问他要不要也建一个“parapavilion”的时候,他立刻表示:“我要把我在维也纳家里的厨房在威尼斯重新建造出来,不过会让它内外颠倒。”他在自己家的厨房里本来就有很多朋友的作品,而现在他要把这些作品原封不动地布置在这件厨房作品的外部,也就是说在这次展览上会额外出现20几位艺术家。而在厨房内部展览的将是Dayanita Singh的投影作品。
郭:上一届双年展着重强调了参与情境与事件性的作品,这是对Pontus Hultén遗产的继承,而且那些展览与行为表演和教育有关。
BC:嗯,这次展览也有一个类似的短期作品。Gelitin打算用一个熔古代玻璃的炉子熔一吨玻璃,然后浇到军械库花园的草坪上。等冷却之后游客就可以在上面行走,在他们脚下就会发生破裂和移动。这是一种社区生活,过来做点什么。另外旁边还有音乐演奏。
郭:那么,换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我们看到,丁托列托的作品富有戏剧性,你选择他的作品是给谁观看的?这种彼此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如何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
BC:丁托列托非常具有试验性,我之所以选择他的作品是为了探讨模式的问题,包括艺术世界的模式、当代艺术公众的模式、古典艺术观众的模式等。我们这代人曾经反抗过在我们德国被称为的“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被标准化了的西方文化,我们要知道哥德、席勒,披着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外衣。我们对此产生了质疑,因为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丧失自我。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讨论问题,什么是文化,什么是艺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化与艺术的基础是什么?
郭:有没有这样的危险:你将丁托列托的作品放在这次展览上是为了在西方高级文化的核心地带建立这些基础?或者说在威尼斯举办的双年展必然会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意味?
BC:当然,有的人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对威尼斯指手画脚,好像威尼斯是个大都会。我们应该诚实一些,从我们实际所了解的情况入手。
— 文/ 比奇·库莱格、郭逸安, 译/ 梁舒涵
- 推荐关键字:“艺术家”,“策展人”,“威尼斯双年展”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