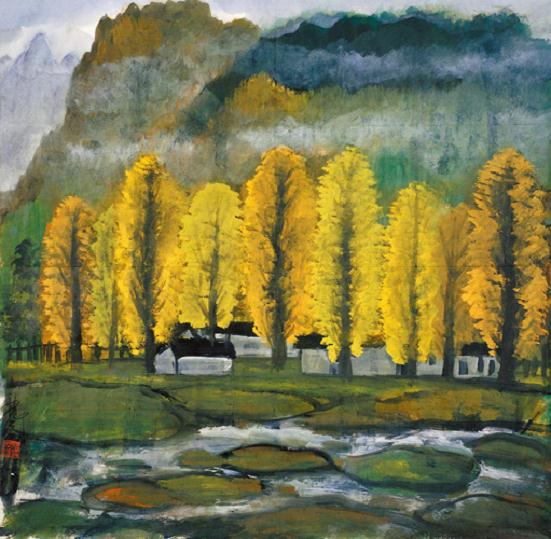1933年弘一大师在泉州韩偓墓道前留影

1942年弘一大师最后讲经处——泉州小山丛竹书院
弘一大师(1880-1942),僧。俗名李叔同,号息霜,又号圹庐老人。异名极多,初名文涛,改名广侯,又改名岩、岸、息、哀、婴或倾。39岁出家,释名演音,字弘一,号晚晴老人,别署笔名多至200余个,以叔同、弘一两名为最著。自谥哀公。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颇具特色的传奇式人物,杰出的艺术大师和爱国高僧。他在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文学、佛学等方面都堪称卓然大家。1918年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后专研戒律,被佛教界奉为中国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1928年初冬到厦门,1942年深秋圆寂于泉州,有14年之久往来于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等地弘法,对近现代闽南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缘际遇,禅居闽南
闽南地处东南一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弘扬佛教文化的漫长行程中奔走了10年的弘一大师,佛学思想已臻于成熟。大师原先并没有想禅居闽南,只是与旧友尤惜阴居士相约拟赴泰国弘法,在1928年12月途经厦门时,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居士、性愿法师和芝峰法师的热情款待而住在南普陀寺,几天后往南安雪峰寺过新年。返厦时在南普陀寺诸法师的恳切相邀下暂留三个月。弘一大师先后又于1930年二下闽南,1932年三下闽南时越发觉得久住闽南是因缘际遇。当时弘一大师有过这样的描绘:“厦门气候四季如春,又有热带之奇花异草甚多,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矣!”这样的气候很适合弘一大师“衣不过三”的苦行生涯。他在致门生刘质平的信中写道:“南闽冬暖夏凉,颇适老病之躯,故未能返浙也。”他到达泉州后,给天津俗侄李晋章的手札又说:“是间气候和暖,桃榴桂菊等一时并开,几不知其为何时序矣。”住下两年后,他仍把这惬意的感受函告故友:“居闽南二载,无有大病。其地寒暑调和,老体颇适宜耳。(暑时不逾四十摄氏度)今岁稻麦丰稔。”
弘一大师还对闽南一带的山川人文景观也极为赏识。他几乎每到一处,都有所感触,曾细致地描绘过清源洞、蓬山毗峰、万寿岩、福林寺等秀美的自然景色。他在致挚友夏丏尊居士的信上说:“净峰寺在惠安县东三十里半岛之小山上,三面临海(与陆地连处仅十分之一),夏季甚为凉爽,冬季北风为山所障亦不寒也。小山之石,玲珑重迭,如书斋几上所供之珍品。”他在给高文显居士的信上写道:“今岁来净峰,见其峰峦苍古,颇适幽居,遂于四月十二日入山,将终老于是矣。”入闽之后,他挂单最长时间的是永春蓬壶普济寺,前后达573天,他称“永春为闽南最安稳之地,山奥地僻,古称桃源。”
宏律传法,爱国爱教
闽南历史上高僧辈出,居士护法众多,特别是以“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泉州为佛教文化重镇的闽南区域,更是弘一大师以弘法为己任,努力实现自己宏愿的良好环境。大师所到之处,不仅受到各寺僧众的热情款待,还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恭请护持。据1938年弘一大师手书记录弘法的《壬丙南闽弘法略志》和《泉州弘法记》中记载他到每一处讲演的题目,均不下二十余种,内容极其丰富。1938年10月28日他写道:“今年在各地弘法甚忙,法缘殊盛。”他在致上海李圆净居士的手札中亦云:“今年在各地(泉、漳、厦、惠)讲经,法缘殊胜,昔所未有。”他在致挚友的一封信中感念良多:“余居闽南十年,受当地人士种种优惠,故于今年往各地弘法,以报答闽南人士之护法厚恩。”弘一大师到漳州弘法时,“乡长、保长等皆喜欢护法,诸事顺适。”1938年农历二月在泉州承天寺讲经时,“听众甚多……青年乃至基督教徒皆甚欢赏。”他高兴地将这种心情告诉丰子恺居士:“乃今岁正月到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在晋江安海时,大师三天的演讲,听众多达700多人。
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法期间,广结法缘,与许多善信往来密切,从大师给数十位居士的信中可以看出,大师对他们关怀备至,循循教诲,甚是感人。大师曾多次为信善者证授皈依,如1935年10月至11月在惠安,就先后六次为70余人证授皈依;1938年2月为泉州崇福寺中的救济院院众近百人授三皈依。弘一大师与闽南各寺僧人关系极为融洽,可以从大师致性愿、太虚、仁开、广义、广空诸法师信中感受到法侣情谊,佛境无我。
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法度过一段顺利和谐的时期。他曾发愿“为宏律而尽形寿”,但时代的风声雨声并没有使他完全忘情世事。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师移锡厦门万石岩,当时厦门战云密布,敌机、敌舰常来骚扰。缁素弟子为大师安危而焦虑,劝请避入内地。大师却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并自题所居为“殉教堂”,表明自己誓与危城共存亡的决心。大师曾感时伤乱,思绪万千,毅然应邀编撰了《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请大家……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为民族争光。”歌曲激昂奋发,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鼓舞了全市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在厦门即将沦陷前的1938年4月的某一天,日寇舰队司令西岗茂泰登岸寻访弘一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弘一大师青年时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大师坚持“在华言华”而拒之。大师直面强敌,大义凛然地说道:“出家人宠辱皆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拒绝了敌酋的“国师”诱请,虽只简短数语,却浸透着大师的人格力量,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嗣后,一些中外报纸均冠以“爱国高僧”的标题予以详细报道。1938年冬季至1941年3月,泉州遭受了日寇飞机接连几十次的狂轰滥炸,死伤频闻,损失极为惨重。弘一大师时居泉州,对日寇的野蛮暴行非常愤慨,他号召僧众说:“我们佛教徒属国民一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乃国民天职……”因此,在他的极力倡导下,晋江县佛教徒联合组成“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选拔壮健僧众教徒集合编训,参与救护伤员,掩埋死难者。在大师的带动影响下,许多佛教徒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
弘一大师于1941年秋禅居晋江福林寺,该寺地处海疆前线,日寇军舰常游弋于永宁深沪海域,泉州开元寺的住持僧为了大师的安全,特派传贯法师前往劝请他回城避难,此时又接到昔年南社诗友柳亚子书赠诗“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大师遂托意回赠《为红菊花说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表达了在敌人气焰方张之时,临危不惧,以民族大义为念,决然奉教的志向,这与其所主张的“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大师所书“念佛不忘救国”之跋语)的爱国思想相印证,可透视大师一片爱国赤诚。
著述宏富,言传身教
弘一大师大部分的佛学著述,都是在闽南完稿的。
首先是校录、论述、编撰大量的佛学著作,这是弘一大师晚年静居闽南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项工作,也是弘一大师所有著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1933年8月在泉州整理《扶桑藏经》,并点校南山律宗三大部。1936年4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东瀛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同年8月闭关厦门鼓浪屿日光别院校录《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大师于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小时。”可见大师点校工作极为辛苦。弘一大师对律学的弘阐,除了讲演和创设南山律学苑外,还编撰校注了一大批律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是他两部重要的律学名著。弘一大师对我国佛学和文化史的最大贡献,就是振兴了湮没700余年的“南山律宗”,因此被世人推崇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师。
其次,弘一大师在闽南还撰写了大量的序、跋、题记、记、传、讲演录、集联、年谱、信札、法事行述等各类散记,文笔幽秀沉稳,意境空灵觉悟,愈至晚年愈趋平淡宁静。代表作有撰于厦门南普陀的《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作于万寿岩的《佛说阿弥陀经义疏撷录序》;还有《闽南行脚散记》、《惠安弘法日记》、《壬丙南闽弘法略志》、《泉州弘法记》、《重兴草庵记》等,至今仍是学术界研究的珍贵资料。
弘一大师在闽南著述、演讲的日子里,曾于1929年11月抵南普陀,协助院方整顿闽南佛学院,现身说法教导学生惜衣惜食惜福,并撰写《悲智训》嘱勉学僧。1934年,弘一大师再次莅院讲学和整顿学风,并于同年3月在厦门南普陀寺创办佛教养正院最为著名,前后达三年之久。大师亲自草拟章程,选定教材,设置课程,平时在讲经授徒的活动中,与青年学僧多接触,注意从思想教育角度出发,训导学僧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大师抱病作了《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的讲演,勉励学僧要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弘一大师以弘律为己任,重视培养律学人才,1933年5月,大师应泉州开元寺方丈转物和尚之请自厦至泉,在开元寺尊胜院开设“南山律学苑”,并亲自教授《四分律会注戒本》及《随机羯磨》,兼学古德格言,以资学僧策励身心。弘一大师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谈到对学僧的教育,关键是进行佛教基本原则的教育。大师曾于1930年早春在泉州承天寺“月台佛学研究社”为诸学僧、居士开设两次有关写字方法的讲座,并帮助学员学习和研究佛学。又于1937年3月28日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向诸学僧作书法讲演,洋洋数千言的文稿,读来倍觉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强调的都是应把学佛理、立大德放在主要位置:“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且没有道德,纵然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不仅熟谙律宗义理,而且身体力行,恪守三皈、五戒、八戒等戒律,过着俭朴清贫的生活,一双芒鞋、一条毛巾,都受用10年之久,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化感染了众多学僧。
翰墨结缘,文艺传人
学贯中西、多才多艺的弘一大师,自出家后,诸艺俱弃绝,惟独对书法恒持不懈,在闽南期间,大师创作了大量颇具哲理性和艺术价值极高的书法作品。形式包括佛经类、楹联类、立轴类、屏条类、杂件小品类及书信简牍类等,数量有上万件。因其往往以书法广结法缘,分赠他人,当时许多名人官绅、僧家居士、青年学生都极其珍爱他那独具禅意的墨宝,纷纷向他求字,所以其书作流布十分广泛,影响颇大。大师作为集儒、释、道于一身的思想家,与同时代其他书法家相比,他的作品更富有内蕴和立体性的张力,被誉为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大师在闽南弘法期间,将佛法与书法之因缘结合得很巧妙。他说:“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戒。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也。”他在给许晦庐居士的信中写道:“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传人,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大师的书艺风格在此期间臻入佳境,他常精楷写经以结善缘,所书《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含宏敦厚,饶有道气,被太虚法师推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他53岁时工严精整写就的《佛说阿弥陀经》,笔意上一洗原有的沉雄,而变为清拔;用笔的挺劲、转折圭角的圆敛,替之以清逸净化了的线条,疏朗修长的形质,整个面貌愈趋于返璞归真,俨然在参悟着一种宗教式的“平淡美”的境界。鲁迅、郭沫若等大文豪都为求得大师一幅墨宝而深感荣幸。鲁迅曾称弘一上人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并说“得李师手书,幸甚!”作为僧人书法家的弘一大师,他的书法艺术与佛教思想犹如水乳交融,呈现出一种超脱空灵、尽善尽美的心灵境界。我们可以从泉州开元寺内的“弘一大师纪念馆”珍藏的数百帧大师遗墨中感受到那蕴藉清质的情感、心绪和澄澈明净的灵魂在跃动。
弘一大师对闽南的文化风物推崇有加,并用他的思想性情、文学意趣抒发了对历代先贤的景仰之情。1930年春,弘一大师驻锡泉州资寿寺,为僧众宣讲《地藏菩萨之灵感》,并到毗邻的温陵养老院寻访前贤遗踪。在“不二祠”凭吊唐诗人欧阳詹,在“小山丛竹书院”补题了朱熹祠“过化亭”匾额,并题记“泉郡素称海滨邹鲁,朱文公尝于东北高阜,建亭种竹,讲学其中,岁久倾圮……余昔在俗、潜心性理,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1933年10月,弘一大师路经泉州西郊潘山,发现“唐学士韩偓墓道”碑,和泪展谒,并在碑旁留影为念。弘一大师很敬佩爱国诗人韩偓,想替韩偓立传,旌表“孤忠奇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师收集了许多资料,交给俗家弟子高文显编著《韩偓评传》一书,大师先后为《韩偓评传》共撰三序,并自撰《香奁集辨伪》一章。由于弘一大师对韩偓的重视,泉州人对韩偓的墓进行了募捐修葺。大师还为泉州开元寺所珍藏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画像题写了《李卓吾像赞》:“由儒入释,悟彻禅机。清源毓秀,万古崔巍。”1933年元旦,弘一大师初到晋江草庵,为庵内“摩尼光佛”石像和明清两代十八位名士在此读书登第的人文胜迹所触动,题写“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联语。
抗日战争期间,大师依然发挥佛教与文化的影响力。他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数百幅分赠各方,写有“最后之胜利”墨宝赠予青年学子,还对小学诸校长说:“小学教育为栽培人材基础,关系国家民族,至重且大。小学教师目下虽太清苦,然人格实至高尚,未可轻易转途。”勖勉僧俗弟子和民众共赴国难。大师还取晚唐诗人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意自勉,自号“晚晴老人”,并自名居室为“晚晴室”,发出了“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的心声,可以说“晚晴室”以意蕴深长的精神内涵,用文化符号寓示了弘一大师晚年对生命节操的确认与坚守,更是大师崇高爱国精神的写照和物化。
弘一大师足迹遍及闽南名山胜水,挂锡弘法过的名刹五十多处。1942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一代高僧弘一大师安详示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世寿六十三,僧腊二十四。圆寂后大师的舍利安放在清源山弥陀岩墓塔中(其中一半灵骨分葬在杭州虎跑寺山中墓塔),供世人瞻仰追思。弘一大师临终绝笔“悲欣交集”所涵盖的深意,既体现了对芸芸众生的真切悲悯,也似乎印证了他遗书中的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以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弘一大师在人生最成熟的阶段选择了闽南。应该说闽南这片土地曾经闪烁过契合大师心境的片片灵光,也许,我们今天已无法捕捉或重现那灵光背后的所有意义,但是,大师将生命中最丰厚的一笔精神文化遗产馈赠给了闽南。闽南,是弘一大师最后的文化驿站。
(作者林长红系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推荐关键字:“弘一法师”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2008上海艺术博览会中的“弘一法师”
- 2008-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