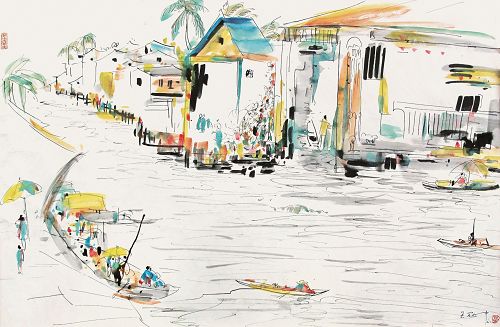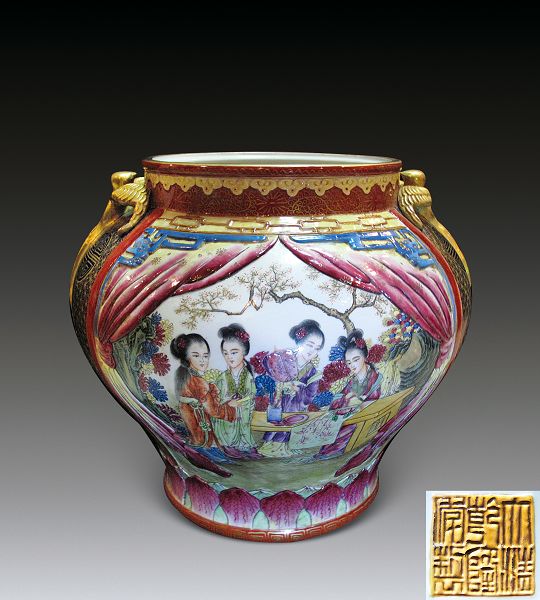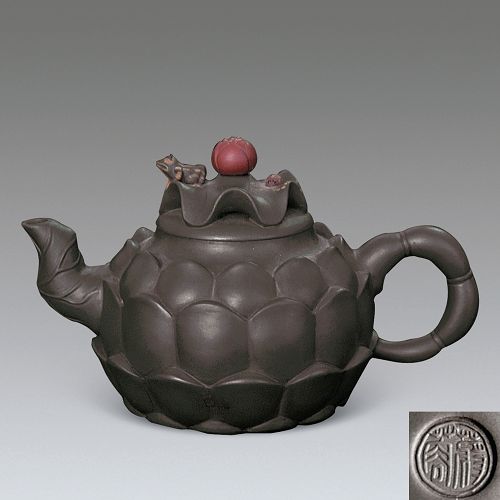许仲敏作品
文:王晴
许仲敏的前卫艺术家身份和他的那些作品一样有趣。
上世纪90年代移居伦敦,见证了当时那里兴起的当代艺术浪潮,出身版画的许仲敏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2004年回国后,他带来了一系列拥有震撼视觉效果和深层社会含义的作品,《转山》、《蛋形》、《隧道》、《云》等也带给了业内不小的惊喜。
用未来主义打造今世的解救行为
“行走”、“繁殖”和“循环”是许仲敏作品中不变的主题,利用高科技和他对光影的敏感,这些元素每一次组合出现,都让人不由自主地开始就地冥想,在一团宗教意味浓重的黑暗中,关于生命如何生存、如何承受、如何结束等问题,也就一并和盘托出了。
“人们很自然地开始考虑生命。反映我这种思想的系列作品始于《桥》。《桥》是在2004年我回国之后,创作的第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像《隧道》和《转山》一样,在作品中运用了同样的媒介、方法和形式。这三个作品密切相关,并且成功连续深刻思考了人类有关“前世”、“现世”和“来世”的轮回。基于以前的经验,《转山》采取设置了一部分如UFO等一样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内容,运用了光和电的特殊效果,并且作品本身创造了一种现代和未来感。作为西藏地区的一种活动,《转山》是一 种“今世”的解救行为。当我在创造我的艺术作品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在“转山”。这是一种自我解救的精神修行过程,充满着苦辣酸甜。”
艺术和宗教中的救赎体验
因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惊人言论,人们开始意识到:传媒业不再只是谣言诽闻的发源地,不再只是强词夺理的场所,不再只是牟取暴利的超级工厂;而是当代社会最具有创造活力的文化形态,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最直接的动力,作为许仲敏作品体系中的对于现实最可信的理论研究方法,他没有能力给出一个解救人类的具体方法,但是关于救赎,许仲敏却是营造这种气氛的高手。
尤其是结合了他自言所谓的来自西藏的精神仪式、建筑模型和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想象之后,便超越了媒介本身,为人们带来了超越符号和技术的更高层面——即一种未来主义和传统礼教被双规之后的和谐精神享受。
“新媒介从事实中获取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和力量,这种事实就是他们比以前所有技术装备似乎能更直接地理解和体验超媒介现实。一种新媒介刚出现在市场,它就暴露其前身仅仅是一种媒介。摄影不错,但电影会动,电影不错,但电视可以直播,电视不错,但网络却是交互式的。每一种新媒介都试图否认其是一种媒介,同时,竭力表明所有其他媒介是媒介,且仅仅是一种媒介。使用旧媒介,你看到的仅仅是其媒介性和它们的技术局限性。但是,通过宣扬自己的直接经验并保留其他装置的间接经验,每一种新媒介不可避免地,唤起了人们对所有媒介的媒介性的理解,及对包括新媒介在内的所有媒介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而只是一种带有符号的技术上的真正认识。”
新作玄机 回归现实感
这次今日美术馆的展览许仲敏带来了两件新作品《梯》和《罂粟》,同样是层层叠叠的树脂人物模型,程序般一步步的不停脚步,色彩斑斓的激光效果,都是整个许仲敏艺术理论体系中不变的代码。
据透露,《梯》被制造成了一个中心挖空的立体圆柱梯形,整个惯例般的“朝圣”过程则发生在挖空的中心部分,观众则需要爬上圆柱梯形外面的梯子的最高处才可以看到整个中心运动的过程。
“所有一切都不能超过现实,至少没有虚构的东西可以超过它。艺术只能呈现现实的一个特殊方面,那就是使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家对现实感的选择上。”
今日美术馆,3月27日-4月12日
- 推荐关键字: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民国]金鼎老字号狮头铺首四方紫砂瓶一对拍卖 -中国收藏网](http://image.socang.com/product/2011/03/29/L0000306532.jpg)